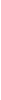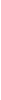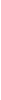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 上一章 | 目录 | 下一章 |
他合上册子的时候,看到了她给这个剧本取的名字:《镜中月光》。
时至午夜,窗外月光,也正好入户。
乌鸦回到卧房,照例有一盏夜灯低亮,床上的人早就睡着。
他不知道她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创作出这个剧本的。故事里的程月和荣伊,像他们,也不像,就如重影。又或许,程月是黎式对自己心内深处的剖析,而荣伊,是她对他的期望延伸化。
荣伊和程月不相衬,难道他和黎式,就般配过吗?
她可是他硬抢来的人。
乌鸦坐到床沿上,重量让床垫轻陷一角,黎式在梦中似乎有感知,出于肌肉记忆,自动向热源靠近。他对她的这种习惯很满意,趁势抱她入怀。
对于剧本,他不是太懂她所写的结局。
是不是有一天,他乌鸦死于非命之时,黎式也会像程月一样,安静的做一个旁观者,顶多再流一滴眼泪,仅作对往事的告别。
他其实懂得荣伊死前的心情。
既希望她就此安静离开,可保往后余生快意安稳,可又希望她能为自己悲伤,以证明曾经拥有过的,也并不只有强迫与妥协。
他放轻动作,摩挲她的侧脸。
有些爱,如镜中月光。
戏中人的爱如是。而睇戏的人,似乎也没有多少分别。
黎式写下程月是荣伊的月亮。可她不知道的是,黎氏女也早已是他陈天雄的月光。
七月初,黎式的毕业任务有了新的工作进展。
校方要求最后呈现的成品,并不仅仅是一个剧本,而是需要学生自己拉到投资,寻找到演员及拍摄团队,身兼数职,做出一部完整的电影。时间可以不似市场上的电影那么长,但其他要求都不能减次。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拉投资这一点,就足够让人头疼。黎式前前后后忙碌了两周,投资人是找到了,但要谈得合适,还差得很远。
动静传到乌鸦哥耳朵里,嘲笑她舍近求远。自己男人就是新北方最大的幕后老板,别说投资,就算喊让当红的影星配上专业的摄影团队直接给她拍出来都没什么问题。
他也是说干就干,马上从派人去了电影公司找到黎式,开门见山问她要什么配置,三天之内就能制备完全。
这阵仗吓得她马上把派来的人摁回去,确认公司同事也没听到任何流言蜚语后,下了班就找某大哥算账,郑重其事地警告他,不允许参与有关自己工作的任何事情,不然她真的会翻脸。
乌鸦无端落一顿批评,回过神后也开始不爽起来。他不理解这个女人的脑袋里在想什么,搞清楚,他是在为她好诶。本以为能得一顿表扬,结果反倒被埋怨。大佬把刚点上的烟摁进烟灰缸,黑着脸拽起外套就往外走。
黎式生着气,但下意识追到门框边上,问外面,“咁夜你仲要去边度啊?”
那男人也生着气,竟还会回答她,“我去瞓(睡)堂口,睇到你这张脸我就烦。”
不爱看别看。她求之不得。
黎式没工夫跟他扯这些有的没的,既然决定不让他插手,她便花更多心思去工作。好在她在新北方的实习工作足够亮眼,办公室的主任听说这件事后,表示可以提供器材上的技术支持,给个员工价,支付60%的经费,但前提是不能够影响到公司正常的业务运营。
这对黎式来说已经是给了很多的方便了,当即答应下来,她的存款不多,便又向上面预支了半年的工资,凑足款项,解决掉了最重要、也是最头疼的问题。虽然说最后还是背靠到新北方,但一个是凭借自己努力,一个是伸手向他低头,乍一看区别不大,其实很大。
资金和硬件设施到位后,就是演员问题了。
她那点少得可怜的预算肯定是请不起明星的,随便拉素人出演,成本是小了,但拍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如人意。黎式用学校电脑画了一张招聘海报,诚邀能够出演女主角和男主角的有志人士,虽然前来报道的人数很多,但符合她心里的角色形象的,很少。不,是几乎没有。
黎式为了能找到更多合适的面孔,自请白天去影棚跟场。可惜看了几日,也都是徒劳无果。午饭时间,她从道具间出来,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色t恤,扎着马尾的女孩站在树下,她的脚边是一个巨大的白色泡沫箱。虽然独自面对几个混道打扮的男人,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
那边的说话声不小,黎式能把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大致剧情老套又常见:女孩的父亲欠了高利贷,无力偿还后就跑路。讨债的找不到爹,就找上了女儿。女孩手里能动的钱都已经给了讨债组,但女孩的外公生病住着院,不能一分钱都不留。她已经在很努力的工作,偿还债务,请债务人再宽限几天。
讨债的几个混子似大发慈悲,才肯多让几日。不过要他们安安静静的走,基本不大可能。其中一个拉开黑皮包,从里面拿出几罐塑料瓶,里面都装着红油漆。扭开了瓶盖就往那个女孩身上倒。
女孩躲避不开,也根本不敢躲,怕惹恼这帮流氓,会作出更下流的事情。
几瓶油漆见底,她身上的白色t恤早就被毁的没形,脸上、头发上也都沾了红色。混子几人扬长而去,女孩蹲在原地,脸埋在膝间看不清神色。
黎式把前情都看在眼里,转身返道具间,再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件大的黑色罩衫。一个女孩身上莫名其妙多了那么多红油漆,无论被谁看见,都是不妥。
但还不等她上前,便听见不远处有人喊名字。
“南粤,你个死人站边度啊,唔知自己要派盒饭?知唔知自己要上工啊?”
蹲在树下的女孩一听到声音就回应,“系!即刻就来!”
她的双手在裤子尚且干净的地方蹭了蹭,站起身来。擦掉了脸上的泪水,搬起泡沫箱子,重新端出了一个礼貌的笑容,仰头见人。
那一瞬间的倔强神色落进了黎式眼里。仰头微笑的那一秒,那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矛盾完美混合,跟她笔下的程月出奇得吻合。连名字都差不多,好似她就是本人活过来了。
一下子恍了神,等反应过来,知去寻人的时候,早就没了这个女孩踪影。黎式几乎是在半秒之内就已经确定了,她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女主角。这名演员,她势在必得。
听人叫名字,似乎叫南月?影棚就那么大,找人应该也算有迹可循。
但黎式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问过去,都没人听过这个名字。直到下班时刻,大部队人员都收工返家,一个扫地的老阿婆听见她到处问讯,自作主张好心插口,“南月?都冇这个人嘅。月?粤晒?叫南粤的倒有一个。”
黎式闻声回头,“阿婆,你话你知南月那个女仔?我唔知系边个字,我就听人喊过。她叫南粤?”
“系啦,系叫南粤。她临时工来的,每日就过来派盒饭。清厕所、整垃圾,别人都唔肯做的工作她都做。女仔人好好,睇我年纪大咗,成日帮我做嘢。”
掏出了随身带着的便签本,黎式直接问,“阿婆,你知唔知她联系方式?或者,你知唔知边头可以揾到她?”
“这个我唔知。不过,你可以去问她做嘢的东家是边个。问东家要可能会有啦。”
“多谢你阿婆。”
按这个思路,黎式找到了后勤部的人。问清楚每天来送盒饭的,是一家叫做罗记的食档。又顺着工作人员给的地址,寻到了罗记的店面所在。
食档很小,横向摆下三幅桌椅,走人都有些拥挤。店中吃饭的人虽算不上多,但正是吃饭的时钟,便不会太空闲。
黎式里外大致看了一圈,也没看到上次的那个白t女孩。刚想向举刀切玫瑰鸡的阿婶打听,就听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
“借过唔该(多谢),小心餐盘”,一个年轻女孩双手交迭之上捧了七八个塑料餐盘,还有个饮了一半的冻柠茶茶杯摇摇欲坠,她看到黎式站在那里,以为她是前来的食客,“小姐,你点单啊?对唔住,我不便咗,你可以去前头餐台。”
黎式认出眼前人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女孩,“我唔需点单,你系唔系南粤?我来揾你。”
对方似乎吓了一跳,收拾残桌的动作一顿,回过头来,上下打量这个穿着文气的女人一番,“我系南粤冇错,你揾我?睇你着衫咁规矩,做先生的?都唔像讨债。喂,不过话先讲正,我冇钱欠你啊。”
“你都放心”,黎式笑了笑,“我来揾你,系问你有无兴趣为我做份工,人工(工资)好商量。”
“做工?咩工?”
黎式从包里拿出了原先那份招聘的广告纸,递过去,“演员。”
“演员?”女孩脸上的表情从疑惑转惊讶,“你揾我演戏啊?madam,你有没有搞错,我,普通人来嘅。”南粤不信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觉得有些好笑。把纸又塞回了黎式手里,转身抹台。她也不信自己会有什么遇见好事的运气。再说她从来都没有演过戏,这种有高难度事情,她自认为自己挑战不来。
黎式被拒绝也不着急,接过纸,从包里翻出了笔,写写画画后又将广告纸折起来,塞进了南粤的围兜口袋里,“我系港大的学生,也系新北方的实习编剧。请你去演我的戏,系觉得你好符合我心目中女主角形象。详细情况都写喺这张纸上,你唔驶担心我系老千(骗子)。你放心,我给出啲片酬,虽然唔够比一线大星,但绝对都比茄哩啡(跑龙套)多啲许。”
南粤听后终于又重新有了反应,她缺很多东西,但最缺的,是钱。日做夜做,一天打四份工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钱吗。
“可我...一没演过戏,二都生得唔够靓啊。”
“编剧是我,制片人亦是我”,黎式听明对方松口,便知事情已经完满一半,“如果你正缺钱,我也可以先支付你一半片酬。剩下的那一半,等你杀青,会即刻送到你手上”
她知道她急需一笔钱去支付医药费,但没有明说。有些话,她知要说半句,留半句。
“你都唔需要即刻覆我,纸上写了我的联系方式,亦写明我做业的地址。你来,既是为我做工,都算帮了我大忙。我系诚心诚意邀请你,欢迎随时来揾我。再见。”
该讲的话都讲完,黎式与其微笑告别。返回去后,静待佳音。
时至午夜,窗外月光,也正好入户。
乌鸦回到卧房,照例有一盏夜灯低亮,床上的人早就睡着。
他不知道她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创作出这个剧本的。故事里的程月和荣伊,像他们,也不像,就如重影。又或许,程月是黎式对自己心内深处的剖析,而荣伊,是她对他的期望延伸化。
荣伊和程月不相衬,难道他和黎式,就般配过吗?
她可是他硬抢来的人。
乌鸦坐到床沿上,重量让床垫轻陷一角,黎式在梦中似乎有感知,出于肌肉记忆,自动向热源靠近。他对她的这种习惯很满意,趁势抱她入怀。
对于剧本,他不是太懂她所写的结局。
是不是有一天,他乌鸦死于非命之时,黎式也会像程月一样,安静的做一个旁观者,顶多再流一滴眼泪,仅作对往事的告别。
他其实懂得荣伊死前的心情。
既希望她就此安静离开,可保往后余生快意安稳,可又希望她能为自己悲伤,以证明曾经拥有过的,也并不只有强迫与妥协。
他放轻动作,摩挲她的侧脸。
有些爱,如镜中月光。
戏中人的爱如是。而睇戏的人,似乎也没有多少分别。
黎式写下程月是荣伊的月亮。可她不知道的是,黎氏女也早已是他陈天雄的月光。
七月初,黎式的毕业任务有了新的工作进展。
校方要求最后呈现的成品,并不仅仅是一个剧本,而是需要学生自己拉到投资,寻找到演员及拍摄团队,身兼数职,做出一部完整的电影。时间可以不似市场上的电影那么长,但其他要求都不能减次。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拉投资这一点,就足够让人头疼。黎式前前后后忙碌了两周,投资人是找到了,但要谈得合适,还差得很远。
动静传到乌鸦哥耳朵里,嘲笑她舍近求远。自己男人就是新北方最大的幕后老板,别说投资,就算喊让当红的影星配上专业的摄影团队直接给她拍出来都没什么问题。
他也是说干就干,马上从派人去了电影公司找到黎式,开门见山问她要什么配置,三天之内就能制备完全。
这阵仗吓得她马上把派来的人摁回去,确认公司同事也没听到任何流言蜚语后,下了班就找某大哥算账,郑重其事地警告他,不允许参与有关自己工作的任何事情,不然她真的会翻脸。
乌鸦无端落一顿批评,回过神后也开始不爽起来。他不理解这个女人的脑袋里在想什么,搞清楚,他是在为她好诶。本以为能得一顿表扬,结果反倒被埋怨。大佬把刚点上的烟摁进烟灰缸,黑着脸拽起外套就往外走。
黎式生着气,但下意识追到门框边上,问外面,“咁夜你仲要去边度啊?”
那男人也生着气,竟还会回答她,“我去瞓(睡)堂口,睇到你这张脸我就烦。”
不爱看别看。她求之不得。
黎式没工夫跟他扯这些有的没的,既然决定不让他插手,她便花更多心思去工作。好在她在新北方的实习工作足够亮眼,办公室的主任听说这件事后,表示可以提供器材上的技术支持,给个员工价,支付60%的经费,但前提是不能够影响到公司正常的业务运营。
这对黎式来说已经是给了很多的方便了,当即答应下来,她的存款不多,便又向上面预支了半年的工资,凑足款项,解决掉了最重要、也是最头疼的问题。虽然说最后还是背靠到新北方,但一个是凭借自己努力,一个是伸手向他低头,乍一看区别不大,其实很大。
资金和硬件设施到位后,就是演员问题了。
她那点少得可怜的预算肯定是请不起明星的,随便拉素人出演,成本是小了,但拍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如人意。黎式用学校电脑画了一张招聘海报,诚邀能够出演女主角和男主角的有志人士,虽然前来报道的人数很多,但符合她心里的角色形象的,很少。不,是几乎没有。
黎式为了能找到更多合适的面孔,自请白天去影棚跟场。可惜看了几日,也都是徒劳无果。午饭时间,她从道具间出来,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色t恤,扎着马尾的女孩站在树下,她的脚边是一个巨大的白色泡沫箱。虽然独自面对几个混道打扮的男人,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
那边的说话声不小,黎式能把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大致剧情老套又常见:女孩的父亲欠了高利贷,无力偿还后就跑路。讨债的找不到爹,就找上了女儿。女孩手里能动的钱都已经给了讨债组,但女孩的外公生病住着院,不能一分钱都不留。她已经在很努力的工作,偿还债务,请债务人再宽限几天。
讨债的几个混子似大发慈悲,才肯多让几日。不过要他们安安静静的走,基本不大可能。其中一个拉开黑皮包,从里面拿出几罐塑料瓶,里面都装着红油漆。扭开了瓶盖就往那个女孩身上倒。
女孩躲避不开,也根本不敢躲,怕惹恼这帮流氓,会作出更下流的事情。
几瓶油漆见底,她身上的白色t恤早就被毁的没形,脸上、头发上也都沾了红色。混子几人扬长而去,女孩蹲在原地,脸埋在膝间看不清神色。
黎式把前情都看在眼里,转身返道具间,再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件大的黑色罩衫。一个女孩身上莫名其妙多了那么多红油漆,无论被谁看见,都是不妥。
但还不等她上前,便听见不远处有人喊名字。
“南粤,你个死人站边度啊,唔知自己要派盒饭?知唔知自己要上工啊?”
蹲在树下的女孩一听到声音就回应,“系!即刻就来!”
她的双手在裤子尚且干净的地方蹭了蹭,站起身来。擦掉了脸上的泪水,搬起泡沫箱子,重新端出了一个礼貌的笑容,仰头见人。
那一瞬间的倔强神色落进了黎式眼里。仰头微笑的那一秒,那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矛盾完美混合,跟她笔下的程月出奇得吻合。连名字都差不多,好似她就是本人活过来了。
一下子恍了神,等反应过来,知去寻人的时候,早就没了这个女孩踪影。黎式几乎是在半秒之内就已经确定了,她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女主角。这名演员,她势在必得。
听人叫名字,似乎叫南月?影棚就那么大,找人应该也算有迹可循。
但黎式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问过去,都没人听过这个名字。直到下班时刻,大部队人员都收工返家,一个扫地的老阿婆听见她到处问讯,自作主张好心插口,“南月?都冇这个人嘅。月?粤晒?叫南粤的倒有一个。”
黎式闻声回头,“阿婆,你话你知南月那个女仔?我唔知系边个字,我就听人喊过。她叫南粤?”
“系啦,系叫南粤。她临时工来的,每日就过来派盒饭。清厕所、整垃圾,别人都唔肯做的工作她都做。女仔人好好,睇我年纪大咗,成日帮我做嘢。”
掏出了随身带着的便签本,黎式直接问,“阿婆,你知唔知她联系方式?或者,你知唔知边头可以揾到她?”
“这个我唔知。不过,你可以去问她做嘢的东家是边个。问东家要可能会有啦。”
“多谢你阿婆。”
按这个思路,黎式找到了后勤部的人。问清楚每天来送盒饭的,是一家叫做罗记的食档。又顺着工作人员给的地址,寻到了罗记的店面所在。
食档很小,横向摆下三幅桌椅,走人都有些拥挤。店中吃饭的人虽算不上多,但正是吃饭的时钟,便不会太空闲。
黎式里外大致看了一圈,也没看到上次的那个白t女孩。刚想向举刀切玫瑰鸡的阿婶打听,就听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
“借过唔该(多谢),小心餐盘”,一个年轻女孩双手交迭之上捧了七八个塑料餐盘,还有个饮了一半的冻柠茶茶杯摇摇欲坠,她看到黎式站在那里,以为她是前来的食客,“小姐,你点单啊?对唔住,我不便咗,你可以去前头餐台。”
黎式认出眼前人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女孩,“我唔需点单,你系唔系南粤?我来揾你。”
对方似乎吓了一跳,收拾残桌的动作一顿,回过头来,上下打量这个穿着文气的女人一番,“我系南粤冇错,你揾我?睇你着衫咁规矩,做先生的?都唔像讨债。喂,不过话先讲正,我冇钱欠你啊。”
“你都放心”,黎式笑了笑,“我来揾你,系问你有无兴趣为我做份工,人工(工资)好商量。”
“做工?咩工?”
黎式从包里拿出了原先那份招聘的广告纸,递过去,“演员。”
“演员?”女孩脸上的表情从疑惑转惊讶,“你揾我演戏啊?madam,你有没有搞错,我,普通人来嘅。”南粤不信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觉得有些好笑。把纸又塞回了黎式手里,转身抹台。她也不信自己会有什么遇见好事的运气。再说她从来都没有演过戏,这种有高难度事情,她自认为自己挑战不来。
黎式被拒绝也不着急,接过纸,从包里翻出了笔,写写画画后又将广告纸折起来,塞进了南粤的围兜口袋里,“我系港大的学生,也系新北方的实习编剧。请你去演我的戏,系觉得你好符合我心目中女主角形象。详细情况都写喺这张纸上,你唔驶担心我系老千(骗子)。你放心,我给出啲片酬,虽然唔够比一线大星,但绝对都比茄哩啡(跑龙套)多啲许。”
南粤听后终于又重新有了反应,她缺很多东西,但最缺的,是钱。日做夜做,一天打四份工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钱吗。
“可我...一没演过戏,二都生得唔够靓啊。”
“编剧是我,制片人亦是我”,黎式听明对方松口,便知事情已经完满一半,“如果你正缺钱,我也可以先支付你一半片酬。剩下的那一半,等你杀青,会即刻送到你手上”
她知道她急需一笔钱去支付医药费,但没有明说。有些话,她知要说半句,留半句。
“你都唔需要即刻覆我,纸上写了我的联系方式,亦写明我做业的地址。你来,既是为我做工,都算帮了我大忙。我系诚心诚意邀请你,欢迎随时来揾我。再见。”
该讲的话都讲完,黎式与其微笑告别。返回去后,静待佳音。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
- 导航
- 设置
- 字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