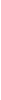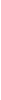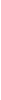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 上一章 | 目录 | 下一章 |
廖希后来很少回忆。
四面空荡,不透光更不透风的空间,客厅里一张荧幕轮播色彩鲜亮的画面,配合音响。
显示屏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使机身发烫,发出哀弱的嗡鸣,叫冷气粗暴地打断了,吹寒霜附着一样的风,初生的热意被吹散去,冷热交织,钟摆一样向两极。
这样的光景日复一日,在同一地点持续上演。
他后来叫人把所有可调的监控画面调出来,再后来是所有留存的影像资料,通过数据媒介,将某日某时某地的路起棋传输到他的眼前。
复数文件攒成庞大的内存,精确客观的度量,从一到十,从十到百,像河流汇聚成海一样宽广,给人无垠的错觉,然而是越不过一个界限,一个日期。
意思是,这世界上有数以万计她留下的痕迹,不会在现在或将来再增重一比特。
路起棋不会再在新一岁来临说“好害怕又好幸福”,不会再在发誓不再熬夜后偷偷通宵被抓到,不会再在被气得脸红时说“你好烦”,不会再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不会怀有期待忐忑捧一个手工蛋糕来办公室等他然后再丢掉,不会在被推开的一瞬间露出绝望的表情,不会对一夜间变得陌生的爱人假装乐观或冷酷但通通没有成功。
通通没有成功。
他就算把路起棋每分每秒,每针每线的人生都咀嚼过,回忆如何爱上她,然后再爱上她,重复重复踏入一条河流。
不会有另一颗心脏,在他体外,远离他的地方安然无恙地跳动。
心跳停在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屏幕上一张脸长得像花苞,细细嫩嫩,像滋饱露水,迎来盛典和太阳,两者都预备歌颂托起她的美丽。
尝试在晚会穿长裙,头发编好再盘起,她试衣服,见他来,从台子上快乐地光脚跳下来,转过身去,露整片背部,说快看哦,破格转型。
他盯在那一片白思考:未免露太多。
但说加内衬,会被路起棋嘲笑是封建脑残。廖希把人扒光了,等她回过神来,裙子变成皱巴巴沾不明液体的破抹布。
路起棋大为光火,短时间去哪里找一条风格不违和版型更适合的裙子,
“还我第一次性感红毯。”
廖希说:“至少第一次已经有过我这个观众,不要遗憾。”
第一次。他们相遇在不早不晚,给他很多有可乘之机的第一次。
人生重要的节点:比如第一次收到录取通知书,前往大学报道,观看自己处女作的播出,收到非常喜欢的剧本先给他分享过目。
再比如第一次劫后余生,飞机在万米高空时遇到故障,乘务人员甚至拿写遗言的纸笔来,他抓她的手掌很紧,路起棋脸吓得煞白,廖希想说点什么安慰,但她先抽出手来捧他的脸左看右看,认真地,轻轻地说:不会死的啦。
多的要像展示勋章生平一般将其一一列举还为时尚早,因为太年轻,要等待一个时机,或者等白头到老。
有次两个人去看极光,还等到一场流星雨,她在一边很安静地哭,也没擦,就等水渍扒在脸皮干掉。
隔一会儿,廖希从身后去抱她,吻她的头发,“想什么?”
路起棋这时候已经停止流泪,慢吞吞地开口,声音落下来好像一片青色的烟,
“想妈妈、爸爸…以前一起看过的星星,和爸爸妈妈。”
后面回去酒店他睡不着,把人叫起来,趁她发脾气前压上去,再牢牢圈住四肢,垂着眼睛看正下方的她,
“路起棋,要不要考虑有一个家。”
路起棋哭完好困,眼皮半阖,嘴巴蠕动,像金鱼在水里咕噜噜吐一串泡泡一样含糊说话,
“什么啊买房子的事干嘛问我…不是早有了吗?不把家当家啊你。”
他低下头,嘴唇蹭在她的耳垂讲悄悄话:“我很快就到法定年龄诶。”
“呃!”
路起棋吓清醒了,生怕他无预兆从哪里拿一个戒指出来,左顾而言他,开始胡言乱语,
“……你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个了,明明未成年就出入网吧,赌场,还无证驾驶,还、还和女同学发生性关系。”
廖希似笑非笑,掐她涨红的脸,“睡觉吧,爱哭鼻子的女同学。”
但路起棋其实说对一件事,他们早就有一个家,当然要一直在一起,多一个仪式,一个称谓,多一重法律认可的关系,当是给家多挂一幅画,多插一枝花。
他先把她晾到一边,自顾自地设想细化,婚礼是一个好时机,合理强迫来宾共历两人风调雨顺的情路,要不要还刻成光碟塞进伴手礼,要不要还在视频影像里加进可以兑换大礼和奖金的口令。
廖希越想越恶趣味,心情在想到路起棋因为社死而出现的悲愤交加的神情时达到顶峰。
她怎么可能还睡得着,此时扒他肩头,恶狠狠地说:“不要背着我想坏事,我都知道。”
心跳停在二十三岁。
是高潮前骤停的交响曲,弦乐停下来,管乐停下来,打击乐停下来,然后下一场雨。
连雨也会停,洗去尘气和血迹,大地变得洁净如新,等天晴,晴到让人怀疑记忆,相信再也不会下那样一场雨。
世界静观其变就行,只是日夜更替,斗转星移,就是在告知,要接受路起棋已死亡的现实。
显示屏轮播到下一个影像文件,廖希在幽蓝色的光,在沙发和茶几间的空隙坐下来,拆一条浓缩补剂,含进嘴里。
他没有刻意不进食,只是经常想不起来要吃东西,酒水填进胃袋,麻痹神经。
年轻的身体尚经得起折腾,没出现什么强有力的报应。
眼前是某天午后的场景,光影由明到暗,爬过女人蜷伏的身体,眠时绵长安静的呼吸,婴儿一样。
困意会传染,细细一支营养品被喝空,塑料片轻飘飘地掉下来。
他见电梯门平移,露出一个小小的身影,不似过往那样窝进一个隐蔽舒适的地点,而是坐到会客的沙发,规规矩矩。
路起棋将带来的袋子放到一边,手心撑在腿侧,指尖无意识地抠住皮面。
她仰起脸,喃喃道:“紧张个屁。”
廖希知道她要等谁。
“路起棋,你现在回去,不要见他。”
廖希蹲下来,目光与她身边的包装袋齐平,仔仔细细,像视线能穿透外壳一样看,里面的东西是要给他的。
他说:不要见他。
路起棋没有理会,目光只是在办公室内胡乱打转,注意力分出大半在一扇门,随后那扇门被推开,有人走进来。
她等来的人无知,愚蠢,自大,看起来什么事都不在意,所以能三言两语,轻而易举打碎一些东西。
从前有人把这些当少一点爱就会枯萎的东西,建一座很大的玻璃房,有宜人的空气和光照,细心打理。
路起棋说:“因为是你说的。”
是她赋予这个人权利。
廖希走到她面前,注视她被泪水打湿的眼睛,红得很可怜的鼻头,颌下像蹭到一片灰,他知道那是面粉。
叫你不听话,粗心大意,路起棋。
廖希伸手到她眼下,擦不到,手指拭过空气,还是用力地徒劳,瘪掉的心脏奄奄一息流出液体,还有潜力多撕开一道血口。
他慢慢地开口,笃定地说:“不要胡说八道,我才不会让你这么伤心。”
视角变成行车记录仪。
熟悉的声音从驾驶座传过来,属于无意识的碎碎念,说好吓人,这人怎么这么开,好想逃跑,弃车再打车吗。
廖希转过头,见她背挺得笔直,表情和握方向盘的姿势都虔诚。
他说:“没有占错道,没有把刹车当油门,还会看后视镜,第一次上路,好聪明。”
以前讨论过为什么突然改变想法去驾校。
路起棋的解释是:“我最近看好几部末日电影,主角开车逃亡的画面情节又多又惊心,代入到情境,没有驾照简直是我最致命的弱点。”
廖希在给她胳膊涂晒伤修护的膏药,顺话茬接下去,
“为了末日逃命?”
“嗯嗯我还订购了末世急救包…等下次还可以去接你下班。”
自然地由末日话题突然跳转到具体生活化的约定。
他吹了吹指腹下那片发红的皮肤,说:“怪浪漫的,路棋棋。”
通往地下的栏杆打开,到目的地,她如释重负,小声地发牢骚:“竟然就这么结束,完成这种壮举,下车时不应该有鲜花夹道欢迎吗?”
没有要等人回应的意思,她边说边拔掉钥匙,车门被推开再合上,发出重重一声响。
地下停车场当然没有鲜花,有灯,有墙壁,有隔一条通道相对的车头。
它最普通平常,无处不见的功能性区域,不该被迁怒厌憎,不该被看作不详的隧洞,诅咒天灾意外在此处发生,在真正的事故,在一场密谋绑架降临前。
他静静坐在那里,说:“那等下次好不好?”
一辆黑色suv由远及近,出现在视野里。
他只是憎恨世间万物。
医院,病房。
路起棋走到窗边,手一扬,带粼粼光斑的固态水滴坠下,不设防地闪进旁人的眼里。
袖口收起,再露出多一点腕上的皮肤,廖希见到未褪净的淤斑。
他动动手指,想摸一下那里。
廖希站在她身后,也和她看到一样的景。
蓝天白云和草地,一株摇晃簌簌的洋紫荆,路起棋凝视被窗框住的一幅画,鲜亮的颜色映进眼睛,整个人暗淡下去。
对话发生在错位一格的齿轮和链条,路起棋也意识到这点,她站在水里,但岸上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岸上。
所以连宣告“我要离开你”都怕自不量力,只是对过去做告别,说:我不等你。
廖希说:“可是我怎么办?路起棋。”
对她而言无用的戒指,对他来说也就一文不值,可是换成他的心呢。
细瘦的手指抓在窗帘,她慢慢地弯起身体,佝成一团,掩盖不住声音中的厌倦。
——“那我不送了。”
他顺从她的意愿转身离开,留她一个人在这里。
廖希知道他出门时叫人去找戒指;知道他感到莫名,烦躁,疑惑,被冒犯,有困兽一撞一撞在发闷的胸口;知道他不知道自己为这个人动摇不安,不知道自己无知愚蠢又自大,不知道这里是最后一次,是两人呼吸相伴的结局。
最后一次没有回头,他从此再也走不出这间病房,每分每秒被困在这里。
路起棋单手抱住膝盖,连抓在窗帘的胳膊都忘记收,直愣愣地出神,不知想些什么,眼眶红得像哭过,其实没有。
谁看了都会心生不忍,要呵护她,认同她,鼓励她,说决意抛弃让她难过的人是正确的决定,祝福她有新的选择,新的生活。
廖希蹲在她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我才不。”
他应该下地狱,应该受永恒的惩罚,被千刀万剐,也应该见到路起棋,长长久久,告诉她:我不可能放手。
他每个细胞打开,都窝藏一颗贪婪卑劣的心,自相矛盾地说我伤害你,哪怕无法挽回,并不是出自本意,可是我爱你。
可是我爱你。
这是梦的最后,他意识到自己要醒来。
廖希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去触摸那只手腕上磨难印记一样的淤斑,对无知无觉的路起棋,艰难地,温柔地问:“痛不痛?”
我的。亲爱的。
在办公室,在停车场,在邮轮上,在酒店,在病房,在最后,你痛不痛。
哪怕任何回答都足够把他变成怪物。
廖希睁开眼,感到四肢无力,肌肉酸痛,猜想是发烧,去翻印象里医药箱的所在地,发现不在原处,他懒得寻找,就地坐下来休息。
从小到大,他生病的次数屈指可数,仅有几次记忆深刻的都在童年,他醒来时家里惯例无人,给棋牌室打去电话,拜托老板找到他妈转达情况。
尝试自己去取高处放药物的盒子,搬来凳椅,站上去还要再垫脚才勉强够到。
他找到需要的,打开外壳,头重脚轻地细细研究刻度,水银体温计从高处落地,一颗颗银色的珠子跳跳蹦蹦,通通滚进他的身体,滚进他的血管里,每一次呼吸,血液循环,叫毒素更深入亲近体内,植根生命。
高烧让鼻喉间的空气都沸热,廖希到卫生间洗一把脸,脸上有水滴往下淌,镜子上也有,镜子里的脸也有。
“路起棋。”
女孩顶一头蓬乱的头发,揉开眼皮,睡衣领口跑偏到肩头,问他要干嘛。
他凑上前去,滚烫的额头对住冰凉的,平静地开口,像报备又像在自语,像肥皂泡升到半空,破掉的时候是没有声音。
“我生病了。”
生病要记得看医生。
“不看。”
为什么?不要任性。
“因为要见你。”
见我?
“见你。”
路起棋没懂,不明其意地指向自己,表情好像在说我不是医生哦,但也笑眯眯。
那你来嘛。
……
廖希换久没上身过的正装,发现宽松不少。
手心几道被玻璃渣划破的口子,总在睡觉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愈合变浅,害他要急匆匆把痂揭掉,撕开下面的薄皮,翻出血肉。
肉体在被作践变得脆弱易折的同时,在血流干前的最后一秒,仍兢兢业业地自救自愈。
宋明拿来晚宴邀请函。
阿觉在一旁神色晦暗,说:“少爷,我总有很不好的预感。”
他一面心中夸赞预感挺准,一面懒洋洋地说:“好不容易让你给我当个司机还费劲。”
廖希到那儿不早不晚,现场和过去参与的并无不同,有几张面孔眼熟,但没人上前靠近,合他心意。
天花板在很远的地方,有灯球吊下来,高高低低,像被处刑,流光溢彩的人头。
他找了一会儿,朝人走过去,顾珩北目光专注在一个方向,方向尽头有爱人,眼里有爱意。
其实用枪会顺手一些,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临时换成刀。
用刀捅进饱含爱意的心脏的胸膛,没什么难度,无意瞥见男人的眼睛,耳边听见风的声音,像某种号哭。
廖希心里升起一种期待和幻想。
为什么用刀,是否在期待眼前这个胸口被染成红色的人也把他一把拉下去,什么都来不及,没有回转余地,从二十层天台坠往地面,内脏粉碎成肉泥,雨水冲刷血迹和残肢断臂。
“啊——”
尖锐的惊叫要划破天花板,也要划破幻想。
眼前只有一双黯淡失焦的瞳孔,和骚动扩散的人群,什么都没有。
他大失所望,给枪上膛,顺刀尖的方向,补上一颗子弹。
后坐力磨消瘦的手掌,伤口牵痛开绽,人重重倒下去,隔厚厚地毯也显得沉重,刚巧旁边有倒好的香槟,亲切的酒精,他想也没想地走过去。
廖希把枪扔到桌上,倚靠桌子坐下来,坐在被惊惧充斥的现场,坐在人群乱踏的地毯,捏一只酒杯,静静地仰起头。
他安然的神色,像是等待这个时刻许久,又像是等待将来的命运。
——
四面空荡,不透光更不透风的空间,客厅里一张荧幕轮播色彩鲜亮的画面,配合音响。
显示屏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使机身发烫,发出哀弱的嗡鸣,叫冷气粗暴地打断了,吹寒霜附着一样的风,初生的热意被吹散去,冷热交织,钟摆一样向两极。
这样的光景日复一日,在同一地点持续上演。
他后来叫人把所有可调的监控画面调出来,再后来是所有留存的影像资料,通过数据媒介,将某日某时某地的路起棋传输到他的眼前。
复数文件攒成庞大的内存,精确客观的度量,从一到十,从十到百,像河流汇聚成海一样宽广,给人无垠的错觉,然而是越不过一个界限,一个日期。
意思是,这世界上有数以万计她留下的痕迹,不会在现在或将来再增重一比特。
路起棋不会再在新一岁来临说“好害怕又好幸福”,不会再在发誓不再熬夜后偷偷通宵被抓到,不会再在被气得脸红时说“你好烦”,不会再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不会怀有期待忐忑捧一个手工蛋糕来办公室等他然后再丢掉,不会在被推开的一瞬间露出绝望的表情,不会对一夜间变得陌生的爱人假装乐观或冷酷但通通没有成功。
通通没有成功。
他就算把路起棋每分每秒,每针每线的人生都咀嚼过,回忆如何爱上她,然后再爱上她,重复重复踏入一条河流。
不会有另一颗心脏,在他体外,远离他的地方安然无恙地跳动。
心跳停在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屏幕上一张脸长得像花苞,细细嫩嫩,像滋饱露水,迎来盛典和太阳,两者都预备歌颂托起她的美丽。
尝试在晚会穿长裙,头发编好再盘起,她试衣服,见他来,从台子上快乐地光脚跳下来,转过身去,露整片背部,说快看哦,破格转型。
他盯在那一片白思考:未免露太多。
但说加内衬,会被路起棋嘲笑是封建脑残。廖希把人扒光了,等她回过神来,裙子变成皱巴巴沾不明液体的破抹布。
路起棋大为光火,短时间去哪里找一条风格不违和版型更适合的裙子,
“还我第一次性感红毯。”
廖希说:“至少第一次已经有过我这个观众,不要遗憾。”
第一次。他们相遇在不早不晚,给他很多有可乘之机的第一次。
人生重要的节点:比如第一次收到录取通知书,前往大学报道,观看自己处女作的播出,收到非常喜欢的剧本先给他分享过目。
再比如第一次劫后余生,飞机在万米高空时遇到故障,乘务人员甚至拿写遗言的纸笔来,他抓她的手掌很紧,路起棋脸吓得煞白,廖希想说点什么安慰,但她先抽出手来捧他的脸左看右看,认真地,轻轻地说:不会死的啦。
多的要像展示勋章生平一般将其一一列举还为时尚早,因为太年轻,要等待一个时机,或者等白头到老。
有次两个人去看极光,还等到一场流星雨,她在一边很安静地哭,也没擦,就等水渍扒在脸皮干掉。
隔一会儿,廖希从身后去抱她,吻她的头发,“想什么?”
路起棋这时候已经停止流泪,慢吞吞地开口,声音落下来好像一片青色的烟,
“想妈妈、爸爸…以前一起看过的星星,和爸爸妈妈。”
后面回去酒店他睡不着,把人叫起来,趁她发脾气前压上去,再牢牢圈住四肢,垂着眼睛看正下方的她,
“路起棋,要不要考虑有一个家。”
路起棋哭完好困,眼皮半阖,嘴巴蠕动,像金鱼在水里咕噜噜吐一串泡泡一样含糊说话,
“什么啊买房子的事干嘛问我…不是早有了吗?不把家当家啊你。”
他低下头,嘴唇蹭在她的耳垂讲悄悄话:“我很快就到法定年龄诶。”
“呃!”
路起棋吓清醒了,生怕他无预兆从哪里拿一个戒指出来,左顾而言他,开始胡言乱语,
“……你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个了,明明未成年就出入网吧,赌场,还无证驾驶,还、还和女同学发生性关系。”
廖希似笑非笑,掐她涨红的脸,“睡觉吧,爱哭鼻子的女同学。”
但路起棋其实说对一件事,他们早就有一个家,当然要一直在一起,多一个仪式,一个称谓,多一重法律认可的关系,当是给家多挂一幅画,多插一枝花。
他先把她晾到一边,自顾自地设想细化,婚礼是一个好时机,合理强迫来宾共历两人风调雨顺的情路,要不要还刻成光碟塞进伴手礼,要不要还在视频影像里加进可以兑换大礼和奖金的口令。
廖希越想越恶趣味,心情在想到路起棋因为社死而出现的悲愤交加的神情时达到顶峰。
她怎么可能还睡得着,此时扒他肩头,恶狠狠地说:“不要背着我想坏事,我都知道。”
心跳停在二十三岁。
是高潮前骤停的交响曲,弦乐停下来,管乐停下来,打击乐停下来,然后下一场雨。
连雨也会停,洗去尘气和血迹,大地变得洁净如新,等天晴,晴到让人怀疑记忆,相信再也不会下那样一场雨。
世界静观其变就行,只是日夜更替,斗转星移,就是在告知,要接受路起棋已死亡的现实。
显示屏轮播到下一个影像文件,廖希在幽蓝色的光,在沙发和茶几间的空隙坐下来,拆一条浓缩补剂,含进嘴里。
他没有刻意不进食,只是经常想不起来要吃东西,酒水填进胃袋,麻痹神经。
年轻的身体尚经得起折腾,没出现什么强有力的报应。
眼前是某天午后的场景,光影由明到暗,爬过女人蜷伏的身体,眠时绵长安静的呼吸,婴儿一样。
困意会传染,细细一支营养品被喝空,塑料片轻飘飘地掉下来。
他见电梯门平移,露出一个小小的身影,不似过往那样窝进一个隐蔽舒适的地点,而是坐到会客的沙发,规规矩矩。
路起棋将带来的袋子放到一边,手心撑在腿侧,指尖无意识地抠住皮面。
她仰起脸,喃喃道:“紧张个屁。”
廖希知道她要等谁。
“路起棋,你现在回去,不要见他。”
廖希蹲下来,目光与她身边的包装袋齐平,仔仔细细,像视线能穿透外壳一样看,里面的东西是要给他的。
他说:不要见他。
路起棋没有理会,目光只是在办公室内胡乱打转,注意力分出大半在一扇门,随后那扇门被推开,有人走进来。
她等来的人无知,愚蠢,自大,看起来什么事都不在意,所以能三言两语,轻而易举打碎一些东西。
从前有人把这些当少一点爱就会枯萎的东西,建一座很大的玻璃房,有宜人的空气和光照,细心打理。
路起棋说:“因为是你说的。”
是她赋予这个人权利。
廖希走到她面前,注视她被泪水打湿的眼睛,红得很可怜的鼻头,颌下像蹭到一片灰,他知道那是面粉。
叫你不听话,粗心大意,路起棋。
廖希伸手到她眼下,擦不到,手指拭过空气,还是用力地徒劳,瘪掉的心脏奄奄一息流出液体,还有潜力多撕开一道血口。
他慢慢地开口,笃定地说:“不要胡说八道,我才不会让你这么伤心。”
视角变成行车记录仪。
熟悉的声音从驾驶座传过来,属于无意识的碎碎念,说好吓人,这人怎么这么开,好想逃跑,弃车再打车吗。
廖希转过头,见她背挺得笔直,表情和握方向盘的姿势都虔诚。
他说:“没有占错道,没有把刹车当油门,还会看后视镜,第一次上路,好聪明。”
以前讨论过为什么突然改变想法去驾校。
路起棋的解释是:“我最近看好几部末日电影,主角开车逃亡的画面情节又多又惊心,代入到情境,没有驾照简直是我最致命的弱点。”
廖希在给她胳膊涂晒伤修护的膏药,顺话茬接下去,
“为了末日逃命?”
“嗯嗯我还订购了末世急救包…等下次还可以去接你下班。”
自然地由末日话题突然跳转到具体生活化的约定。
他吹了吹指腹下那片发红的皮肤,说:“怪浪漫的,路棋棋。”
通往地下的栏杆打开,到目的地,她如释重负,小声地发牢骚:“竟然就这么结束,完成这种壮举,下车时不应该有鲜花夹道欢迎吗?”
没有要等人回应的意思,她边说边拔掉钥匙,车门被推开再合上,发出重重一声响。
地下停车场当然没有鲜花,有灯,有墙壁,有隔一条通道相对的车头。
它最普通平常,无处不见的功能性区域,不该被迁怒厌憎,不该被看作不详的隧洞,诅咒天灾意外在此处发生,在真正的事故,在一场密谋绑架降临前。
他静静坐在那里,说:“那等下次好不好?”
一辆黑色suv由远及近,出现在视野里。
他只是憎恨世间万物。
医院,病房。
路起棋走到窗边,手一扬,带粼粼光斑的固态水滴坠下,不设防地闪进旁人的眼里。
袖口收起,再露出多一点腕上的皮肤,廖希见到未褪净的淤斑。
他动动手指,想摸一下那里。
廖希站在她身后,也和她看到一样的景。
蓝天白云和草地,一株摇晃簌簌的洋紫荆,路起棋凝视被窗框住的一幅画,鲜亮的颜色映进眼睛,整个人暗淡下去。
对话发生在错位一格的齿轮和链条,路起棋也意识到这点,她站在水里,但岸上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岸上。
所以连宣告“我要离开你”都怕自不量力,只是对过去做告别,说:我不等你。
廖希说:“可是我怎么办?路起棋。”
对她而言无用的戒指,对他来说也就一文不值,可是换成他的心呢。
细瘦的手指抓在窗帘,她慢慢地弯起身体,佝成一团,掩盖不住声音中的厌倦。
——“那我不送了。”
他顺从她的意愿转身离开,留她一个人在这里。
廖希知道他出门时叫人去找戒指;知道他感到莫名,烦躁,疑惑,被冒犯,有困兽一撞一撞在发闷的胸口;知道他不知道自己为这个人动摇不安,不知道自己无知愚蠢又自大,不知道这里是最后一次,是两人呼吸相伴的结局。
最后一次没有回头,他从此再也走不出这间病房,每分每秒被困在这里。
路起棋单手抱住膝盖,连抓在窗帘的胳膊都忘记收,直愣愣地出神,不知想些什么,眼眶红得像哭过,其实没有。
谁看了都会心生不忍,要呵护她,认同她,鼓励她,说决意抛弃让她难过的人是正确的决定,祝福她有新的选择,新的生活。
廖希蹲在她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我才不。”
他应该下地狱,应该受永恒的惩罚,被千刀万剐,也应该见到路起棋,长长久久,告诉她:我不可能放手。
他每个细胞打开,都窝藏一颗贪婪卑劣的心,自相矛盾地说我伤害你,哪怕无法挽回,并不是出自本意,可是我爱你。
可是我爱你。
这是梦的最后,他意识到自己要醒来。
廖希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去触摸那只手腕上磨难印记一样的淤斑,对无知无觉的路起棋,艰难地,温柔地问:“痛不痛?”
我的。亲爱的。
在办公室,在停车场,在邮轮上,在酒店,在病房,在最后,你痛不痛。
哪怕任何回答都足够把他变成怪物。
廖希睁开眼,感到四肢无力,肌肉酸痛,猜想是发烧,去翻印象里医药箱的所在地,发现不在原处,他懒得寻找,就地坐下来休息。
从小到大,他生病的次数屈指可数,仅有几次记忆深刻的都在童年,他醒来时家里惯例无人,给棋牌室打去电话,拜托老板找到他妈转达情况。
尝试自己去取高处放药物的盒子,搬来凳椅,站上去还要再垫脚才勉强够到。
他找到需要的,打开外壳,头重脚轻地细细研究刻度,水银体温计从高处落地,一颗颗银色的珠子跳跳蹦蹦,通通滚进他的身体,滚进他的血管里,每一次呼吸,血液循环,叫毒素更深入亲近体内,植根生命。
高烧让鼻喉间的空气都沸热,廖希到卫生间洗一把脸,脸上有水滴往下淌,镜子上也有,镜子里的脸也有。
“路起棋。”
女孩顶一头蓬乱的头发,揉开眼皮,睡衣领口跑偏到肩头,问他要干嘛。
他凑上前去,滚烫的额头对住冰凉的,平静地开口,像报备又像在自语,像肥皂泡升到半空,破掉的时候是没有声音。
“我生病了。”
生病要记得看医生。
“不看。”
为什么?不要任性。
“因为要见你。”
见我?
“见你。”
路起棋没懂,不明其意地指向自己,表情好像在说我不是医生哦,但也笑眯眯。
那你来嘛。
……
廖希换久没上身过的正装,发现宽松不少。
手心几道被玻璃渣划破的口子,总在睡觉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愈合变浅,害他要急匆匆把痂揭掉,撕开下面的薄皮,翻出血肉。
肉体在被作践变得脆弱易折的同时,在血流干前的最后一秒,仍兢兢业业地自救自愈。
宋明拿来晚宴邀请函。
阿觉在一旁神色晦暗,说:“少爷,我总有很不好的预感。”
他一面心中夸赞预感挺准,一面懒洋洋地说:“好不容易让你给我当个司机还费劲。”
廖希到那儿不早不晚,现场和过去参与的并无不同,有几张面孔眼熟,但没人上前靠近,合他心意。
天花板在很远的地方,有灯球吊下来,高高低低,像被处刑,流光溢彩的人头。
他找了一会儿,朝人走过去,顾珩北目光专注在一个方向,方向尽头有爱人,眼里有爱意。
其实用枪会顺手一些,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临时换成刀。
用刀捅进饱含爱意的心脏的胸膛,没什么难度,无意瞥见男人的眼睛,耳边听见风的声音,像某种号哭。
廖希心里升起一种期待和幻想。
为什么用刀,是否在期待眼前这个胸口被染成红色的人也把他一把拉下去,什么都来不及,没有回转余地,从二十层天台坠往地面,内脏粉碎成肉泥,雨水冲刷血迹和残肢断臂。
“啊——”
尖锐的惊叫要划破天花板,也要划破幻想。
眼前只有一双黯淡失焦的瞳孔,和骚动扩散的人群,什么都没有。
他大失所望,给枪上膛,顺刀尖的方向,补上一颗子弹。
后坐力磨消瘦的手掌,伤口牵痛开绽,人重重倒下去,隔厚厚地毯也显得沉重,刚巧旁边有倒好的香槟,亲切的酒精,他想也没想地走过去。
廖希把枪扔到桌上,倚靠桌子坐下来,坐在被惊惧充斥的现场,坐在人群乱踏的地毯,捏一只酒杯,静静地仰起头。
他安然的神色,像是等待这个时刻许久,又像是等待将来的命运。
——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
- 导航
- 设置
- 字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