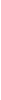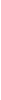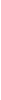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 上一章 | 目录 | 下一章 |
好消息算不上,但总归也不是坏消息。
廖希擦掉手上的水痕,不远处的桌面,未熄的手机屏幕上是助理发来房屋产权变更完成的进度汇报,被赠与人一栏写路起棋的大名。
一般般,勉强过得去的见面礼。
把刚切好的西瓜端上,他一手推开虚掩的房门,对上一张眼眶红红的哭脸,羽睫被压垂,泪珠淌到下巴。
廖希呼吸一滞。
路起棋吸了吸鼻子,视线从手机屏幕移开,看见门边的他了,用手背利落地擦两下脸。
她从椅子上跳下来,走到跟前,胳膊上举,掌心在他眼前啪地一合,声响清脆。
“回神咯。”
开口时还带着浓重的鼻音,路起棋仰脸对他弯起眼睛,解释说自己刚在看一部短剧。
“快到结局莫名其妙就开虐,讲男女主人妖殊途注定要分开,发神经这剧情。”
她抱怨着,又转身回到座位,在椅子上踢踢小腿,语气一变,轻快地催促道:“西瓜西瓜。”
廖希把玻璃碗放到她手边。
碗口堆起一个顶,切成适口大小的粉红色果肉码放,水津津馋人的外貌。路起棋咬进一块,半边腮帮子鼓鼓,咀嚼速度逐渐放缓,眼睑半垂,若有所思。
他拉开旁边的椅子坐下,视线仍在她脸上,解释说:“从冰箱拿出来多晾了一会儿,没那么凉。”
路起棋点头,说:“噢。”
少吃生冷垃圾食品。医生更早前的劝诫浮在耳边。
也是高二那年落下的遗留问题,那时她欠佳的心理状态连累到生理,加上学业压力,有好一段时间,体重悬在很极限的低谷期,三天两头要发烧生病,廖希不得不对路起棋的生活习惯进行制约。
“不得不”说明这项工作具体开展得并不顺利。
一是路起棋内在其实比外表叛逆许多,不大爱受人管教,在廖希面前窝里横的本性更暴露无遗。
二是由廖希担任纪律委员这件事本身就较为离谱,哪怕当前版本的他心智成熟,社会经验丰富,拿捏她更唯手熟尔,但此人在路起棋心中的权威还比不上傅采夏,适合与她做同谋,而不是肃正不良嗜好。
果不其然,没收到抗议,廖希揭晓预留好的惊喜:“还剩半个,等下给你榨西瓜冰。”
“好耶。”
她懒洋洋地欢呼,在扶手上支起半边脑袋,掌腹托出一捧丰腴的脸颊肉,折起的手腕骨肉停匀。
总归路起棋也不是不识好歹的人,后边在这样“一个巴掌十个枣”的监督模式下顺利回归正常体重,免疫力同步渐长,她现在早已脱离那段脆皮时期。
话说回来——
路起棋啜吸口腔里淋漓清甜的汁水,叫果肉碎成绵软的丝瓤,嘀嘀咕咕:“好想吃脆皮雪糕。”
“你知不知道那个…”紧接着又开口,只是无目的闲聊,路起棋讲一个品牌名,“它家做汽水的,菠萝和西瓜味最出名。”
家里冰箱里会常备各式各样的冰淇淋,汽水则未必,廖希不动声色地问:“想喝吗?”
路起棋说:“不想,要喝你榨的西瓜冰。”
这西瓜是她在路边的移动摊位挑的,廖希出力抱回家,一大个应季的沙沙甜甜,她扎一块果肉递到他唇边,很慷慨地说:“请你吃。”
整个上半身也倾靠过来,廖希吃她喂过来的,垂下眼眸,视线以内是修长的脖颈和拉伸开的锁骨,颈侧有一粒小小的蚊子包,淡粉色的凸起,靠近看才显眼。
“今天出门了?”
未等回答,他稍低下头。
她脖上系一根颈链缀满钻,随呼吸闪动鳞状的光,廖希张口咬住链子下方的小环,唇瓣贴在颈间,感知到微小的脉动,舌尖继而濡湿皮肤。
湿热的触感呵在脖根,有些痒,路起棋倒没躲,往链子里堪堪伸进一个指节,勾起向外扯,拧起眉提醒道:“沾到口水了。”
“嗯。”
廖希含糊应答,从那块舔湿的皮肤撤开一点,舌尖顶出湿漉漉的钻环,又去有一下没一下啄那颗圆圆的蚊子印,显然不觉得自己有做错。
“没见过,最近买的?”
指颈链。
路起棋仰头晾出下颌线,小幅度晃动给他展示。
“上次回家,我正好把你爸爸送的那个寓意多子多福,利于生育的手串转送给我妈了,她就回赠了这个,好看吗?”
手串其实路起棋没有戴过,但收到之后短短一个月里,廖希和她各自意外捡到一窝流浪动物回家。虽然暂养不用事事亲力亲为,为其寻找领养人是一项实打实的大工程,现在家里变得拥挤不少。
不管是不是巧合,这手串的使命发挥得太立竿见影太灵,不能再继续冒险,还是交给真正有需要的人更合适。
“还可…以?”
他漫不经心掂起链子一角,尾音略微迟疑。
“怎么?”路起棋歪歪脑袋,当然不会以为他是失踪已久的孝心觉醒。
廖希问:“你们和好了?”
和好这个词有些严重。
近几年里,她对路彤一直保持着不拒绝不主动的态度,重大节假日,升学和成人礼时都没有表达出与她问候交流的意愿。
落到对方眼里就是亲生女儿自发的疏离背刺,路起棋直接或间接听到过很多类似“翅膀硬了”“白眼狼”的指责。
这次假期是路老太太嘴硬心软,怕路彤真寡郁出病来,劝她去首都陪住几天。路起棋没拒绝,拿手串和其他礼物过去敲门的时候,竟然隐约看到了对方眼中受宠若惊的诧异。
但这不等同于两人关系向好,她认为把路彤当普通长辈是可以,心理上划归得再亲近些,回忆起一些做法动机也太让人寒心。
“谁知道。”路起棋向后靠上椅背,回答得兴致缺缺,“我无意和任何人维系深刻的爱恨情仇。”
“——除了你哦。”
语气一转,她声音变柔软,淋枫糖浆的棉花糖,低头用鼻尖蹭蹭他的,言行合一的亲昵。
四目相对,带各自体温的呼吸也是,路起棋一字字叫他名:“廖希。”
“你这个应激反应时不时发作一下,要不要联络我之前做咨询的老师,聊一聊天也可以,他还蛮有名的。”
“原来在惦记这个。”他手掌扶在她后脑勺,上前碰一下唇角。
路起棋过去在遥城的咨询师,廖希作为称职的男友,当然要有所了解:业内评价良好,颇具口碑。
只是这提议不太妥当,毕竟两年前逼迫这位资深敬业的心理咨询师呈文又口述,事无巨细泄露一位名为路起棋的病人档案和对话细节——简称“渎职”的要犯,如果还要上门求医,太厚颜无耻。
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这会儿振振有词:“涉及男朋友的身心健康,我超关心好不好。”
廖希想了想,干脆把她抱到腿上坐,窝在颊边咬耳朵:“其实有你就行。”
“好会见缝插针。”
他低声笑:“说真话也不让吗。”
路起棋沉默地伸手搂紧他的脖子,没再说话。
偶尔有一些时刻,她投入到某种情绪时不经意对上视线,或是醒来见廖希在枕边看自己,会露出刚刚在门边时那样的表情和眼神。
她一开始只是觉得似曾相识,仿佛很久以前在梦里见过同样的眼睛,但要回忆,又很难具体到细节,只当是他难释的愧意更多,不好她单方面说没关系的,慢慢来。
但久了就回过味来,他在眼前,像个浸湿的、永远不会干燥的伤口,路起棋没办法视若无睹。
一次两人有事分别,路起棋走出几百米远,被路口窜出的摩托车吓跌倒,一点点擦破皮和淤青,没什么大问题,只是要起身时发现t恤上的别针和牛仔裤破洞勾到一起,解开花了点时间。
很快有人上来搀她,面生但不是好心路人,开口叫她“路小姐”。站直了,隐约听见哪里传来不寻常的声响。
后面知道廖希隔一条路出车祸,是朝她这边过来的时候无视信号灯,倒霉的司机刹车不及,他右腿被撞成骨折。
路起棋事后真的蛮生气,不是玩笑打闹居多那种,检查过程里保持冷脸,对伤者更没施舍眼神和问候,转身就走。
没走出几步,身后传来噼里哐啷的动静,廖希侧身摔下来,电脑连带床头很多杂物洒落一地。
故意的,拐杖就放在床边。
“明明你叫我什么事都以自己人身安全为先。”
她还是挪腿回去,把他以前的原话也还回去。两个人都知道路起棋见弱小,迷你的胆量会膨胀一些,那时候廖希说:不是让你改了,但只有这一点,好不好。
好不好,他像央哄小孩,而不是此刻她复述的语气像风干腊肠硬邦邦。
“喝水会呛,吃饭会噎,走路会崴脚,都是日常小概率的事件,我下次屁股和手着地可能也是准备做breaking,廖希,我们要一起生活很久,放松一点,你这样——”不累吗?
路起棋居高临下地看他,眉心拧紧,没把话说尽。
她再迟钝,长期被寸步不离的安保力度环绕在周,加上枕边人紧绷的状态,藏得再好也总能察觉到一二。
他装没事人,带几分示好的意味:“宝宝,做那个容易骨折,记得戴护具。”
路起棋倒吸一口气——有人完了。
“我知道。”他突然说。
廖希半坐在地的模样好狼狈,仰头巴巴拉她的手,姿态放得低,语气像赌气又像认命。
他说:“我知道,路起棋,我没办法。”
以僵局收场,后面还是慢慢和好,他搭很多台阶过来,保证路起棋可以顺势不知不觉地走下去。
没办法,她也没办法。
人总有无解的时期和情绪。路起棋也有,被旁人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刺痛,全宇宙都惹到她。
廖希时有承载她莫名发难。
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可不可以别问。送你这朵花好不好。不好。两朵好不好。不好。不送呢。也不好。
倾向自厌自毁的瞬间也不少,男孩子的花无法消愁,男孩子的花容月貌同样无法。那时“死”字还没成为谶言晦词,路起棋事后在床上恹恹地哭完,又发狠话说一起死。
人要怎么把另一个人占为己有,她钻牛角尖到底,总不能真啖肉饮血。
如果她足够健壮聪明有权有势,以彼时的精神状态,会试图把人囚禁上演强制爱小黑屋场景也不一定。
……话说回来,假想中的受害者本人一旦知晓她这个想法,不说喜形于色,绝对跃跃欲试。
——居然是回合制!不过是回合制!
路起棋苦中作乐地想:廖希只是这个时期比较长,比较不外显,比较多多折磨他自己。
她搞不清这是否称得上是义气。路起棋心智未开化前就被教导养成习惯:幼儿园的小朋友今天送自己一支仙女棒,第二天她要带一个小汽车。
这回送的兜里塞不下,一整个书包也塞不下。衣食住行,加放在襁褓里时刻被托举抚平的情绪,花时间金钱和精力要多少,路起棋是养一棵以光合作用为生的植物都不易的人。
想起以前阿姨从国外回来,一同吃家宴时补发压岁钱,小辈里,路起棋收到尤其厚的一迭。
对大呼不公平的其他人给出解释:“棋棋跟我关系好,又是女孩。”
接着老生常谈,开展一些饭桌常驻主题,说女孩子要有富足的成长环境,长大了才不容易被外面心怀不轨油嘴滑舌的男人骗。
阿姨怅然道:“时间很快的唷。”
路起棋当时在上初中,爸爸一边接对面碰过来的杯子,一边说:“这个话题对我很残忍。”
扭头对她提醒:“到时候一定找一个像爸爸爱妈妈一样爱你的。”
妈妈翻了个白眼,“那不然呢?”
爸爸说:“…好吧,要像妈妈爱你一样爱你。”
妈妈立刻正色,用“不可能”的表情说:“这有点难。”
饭桌上的大家目光集中到一处,笃定有很多小男生给她递情书。路起棋对这个场景头大,急于转移话题,想这岂止有点难,说哦哦我们最近学到蜀道难。
心里的想法会失礼一点,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带着天然的自满优越和嫌弃:男生吗?又丑又吵又讨厌的生物。
眼前这个男人,和丑和吵和讨厌绝对搭不上关系,爱要怎么衡量相较,用刻度尺,用量筒,用天平,难于上青天是在表述难的最高级,路起棋知道他是没有她会死掉的程度。
偶尔也会反思,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动辄要死要活的琼瑶剧形态。
她在幸福浓度很高的环境里长大,不缺任一一种关爱,动心也是恰逢适宜的年纪和荷尔蒙,是样貌加性格加外在表现都合意的对象,繁重的学业间隙给足情绪。
理想健康的恋爱关系是怎样,不利于自己和对方就得终止拨正,好比那次半途而废的分手,她状态不好,也是仔细斟酌利害。
如果要给现在的生活评价,路起棋也会说“很好”。当下维持不错的人际关系,念不错的学校拿奖学金,去年底拿到结果不错的体检报告。“不错”讲起来更符合中庸之道,弹性大容错高,然而很好就是真的很好,没有什么矫饰的成分。
二者间的变量在于一个人,廖希悱恻地刺穿她温吞的壳,然后一整个变成望不到底的温柔乡。
温室里什么都养,害怕或是担忧,最适宜欲念滋长。理性无时不在敲钟,对立面的私欲嘲笑她:你不就想要这个。
想要什么,是路起棋说完一起死,廖希想也不想回“行啊”,同时伸出手臂无限耐心珍视地抱她擦眼泪。
一想到是这个人,她不由病态觉得:打不过就加入,蛮快乐的。
路起棋不会忘记给玩伴带小汽车,而从没有给收过的情书回函。因此这无关仁义礼智,不是知恩图报,是情难自禁,求仁得仁。
爱意同样可以饲喂爱,回溯最早最早的见色起意,弃之可惜的塑料袋被撑成暴食症一般不知饥饱的胃,路起棋心甘情愿地放下戒心,不是向世界和陌生人的戒心,是驱乎本能,写在基因里的疼就躲避痒就笑。
好,都可以。
她伸手用掌心盖住面前的眼睛,把自己填进一处伤口,等血肉长在一起,至少不会溃烂下去。
廖希要什么就得到,要分不开就分不开,生命各处长连在一起,肉体和灵魂彼此咬合,她这么爱胡思乱想,朝三暮四,也会认为,除了和这个人共度一生,没有第二种可能。
感知到睫毛轻轻地搔在手心,眼皮鼓起同样脆弱地抖,像一尾金鱼游,痒痒的,愈合时皮肉增生的错觉。
路起棋说:“好,不会不要你。”
她撤回手,让光掷进去,墨汪汪一面镜照出路起棋的脸,照出圆圆的杏眼弯成月,笑得很可爱地说:“没事的,我爱你,我也爱你。”
话音落下,一方空间只剩安静,室内的温度一达标,冷气就偃息,窗外的知了叫不停,芭蕉叶被烘得绿,油,皱。
并非盛典佳节,黄历上值得圈定的好日期。
路起棋说“爱”,酷似庄严的宣誓,或是交换承诺,抹平时差,无意回望一双乞怜的眼睛,梦里醒来时都见,上天入地两个人的秘密基地。
这是最平常的一个午后,天气预报显示此时气温在三十二度,遥城入夏以来的高温纪录发生在一周前,炙人惊心的三十九度,标红的数字之下,记无关紧要的一笔。
桌上西瓜还剩半碗,她同他肝胆相照。
廖希擦掉手上的水痕,不远处的桌面,未熄的手机屏幕上是助理发来房屋产权变更完成的进度汇报,被赠与人一栏写路起棋的大名。
一般般,勉强过得去的见面礼。
把刚切好的西瓜端上,他一手推开虚掩的房门,对上一张眼眶红红的哭脸,羽睫被压垂,泪珠淌到下巴。
廖希呼吸一滞。
路起棋吸了吸鼻子,视线从手机屏幕移开,看见门边的他了,用手背利落地擦两下脸。
她从椅子上跳下来,走到跟前,胳膊上举,掌心在他眼前啪地一合,声响清脆。
“回神咯。”
开口时还带着浓重的鼻音,路起棋仰脸对他弯起眼睛,解释说自己刚在看一部短剧。
“快到结局莫名其妙就开虐,讲男女主人妖殊途注定要分开,发神经这剧情。”
她抱怨着,又转身回到座位,在椅子上踢踢小腿,语气一变,轻快地催促道:“西瓜西瓜。”
廖希把玻璃碗放到她手边。
碗口堆起一个顶,切成适口大小的粉红色果肉码放,水津津馋人的外貌。路起棋咬进一块,半边腮帮子鼓鼓,咀嚼速度逐渐放缓,眼睑半垂,若有所思。
他拉开旁边的椅子坐下,视线仍在她脸上,解释说:“从冰箱拿出来多晾了一会儿,没那么凉。”
路起棋点头,说:“噢。”
少吃生冷垃圾食品。医生更早前的劝诫浮在耳边。
也是高二那年落下的遗留问题,那时她欠佳的心理状态连累到生理,加上学业压力,有好一段时间,体重悬在很极限的低谷期,三天两头要发烧生病,廖希不得不对路起棋的生活习惯进行制约。
“不得不”说明这项工作具体开展得并不顺利。
一是路起棋内在其实比外表叛逆许多,不大爱受人管教,在廖希面前窝里横的本性更暴露无遗。
二是由廖希担任纪律委员这件事本身就较为离谱,哪怕当前版本的他心智成熟,社会经验丰富,拿捏她更唯手熟尔,但此人在路起棋心中的权威还比不上傅采夏,适合与她做同谋,而不是肃正不良嗜好。
果不其然,没收到抗议,廖希揭晓预留好的惊喜:“还剩半个,等下给你榨西瓜冰。”
“好耶。”
她懒洋洋地欢呼,在扶手上支起半边脑袋,掌腹托出一捧丰腴的脸颊肉,折起的手腕骨肉停匀。
总归路起棋也不是不识好歹的人,后边在这样“一个巴掌十个枣”的监督模式下顺利回归正常体重,免疫力同步渐长,她现在早已脱离那段脆皮时期。
话说回来——
路起棋啜吸口腔里淋漓清甜的汁水,叫果肉碎成绵软的丝瓤,嘀嘀咕咕:“好想吃脆皮雪糕。”
“你知不知道那个…”紧接着又开口,只是无目的闲聊,路起棋讲一个品牌名,“它家做汽水的,菠萝和西瓜味最出名。”
家里冰箱里会常备各式各样的冰淇淋,汽水则未必,廖希不动声色地问:“想喝吗?”
路起棋说:“不想,要喝你榨的西瓜冰。”
这西瓜是她在路边的移动摊位挑的,廖希出力抱回家,一大个应季的沙沙甜甜,她扎一块果肉递到他唇边,很慷慨地说:“请你吃。”
整个上半身也倾靠过来,廖希吃她喂过来的,垂下眼眸,视线以内是修长的脖颈和拉伸开的锁骨,颈侧有一粒小小的蚊子包,淡粉色的凸起,靠近看才显眼。
“今天出门了?”
未等回答,他稍低下头。
她脖上系一根颈链缀满钻,随呼吸闪动鳞状的光,廖希张口咬住链子下方的小环,唇瓣贴在颈间,感知到微小的脉动,舌尖继而濡湿皮肤。
湿热的触感呵在脖根,有些痒,路起棋倒没躲,往链子里堪堪伸进一个指节,勾起向外扯,拧起眉提醒道:“沾到口水了。”
“嗯。”
廖希含糊应答,从那块舔湿的皮肤撤开一点,舌尖顶出湿漉漉的钻环,又去有一下没一下啄那颗圆圆的蚊子印,显然不觉得自己有做错。
“没见过,最近买的?”
指颈链。
路起棋仰头晾出下颌线,小幅度晃动给他展示。
“上次回家,我正好把你爸爸送的那个寓意多子多福,利于生育的手串转送给我妈了,她就回赠了这个,好看吗?”
手串其实路起棋没有戴过,但收到之后短短一个月里,廖希和她各自意外捡到一窝流浪动物回家。虽然暂养不用事事亲力亲为,为其寻找领养人是一项实打实的大工程,现在家里变得拥挤不少。
不管是不是巧合,这手串的使命发挥得太立竿见影太灵,不能再继续冒险,还是交给真正有需要的人更合适。
“还可…以?”
他漫不经心掂起链子一角,尾音略微迟疑。
“怎么?”路起棋歪歪脑袋,当然不会以为他是失踪已久的孝心觉醒。
廖希问:“你们和好了?”
和好这个词有些严重。
近几年里,她对路彤一直保持着不拒绝不主动的态度,重大节假日,升学和成人礼时都没有表达出与她问候交流的意愿。
落到对方眼里就是亲生女儿自发的疏离背刺,路起棋直接或间接听到过很多类似“翅膀硬了”“白眼狼”的指责。
这次假期是路老太太嘴硬心软,怕路彤真寡郁出病来,劝她去首都陪住几天。路起棋没拒绝,拿手串和其他礼物过去敲门的时候,竟然隐约看到了对方眼中受宠若惊的诧异。
但这不等同于两人关系向好,她认为把路彤当普通长辈是可以,心理上划归得再亲近些,回忆起一些做法动机也太让人寒心。
“谁知道。”路起棋向后靠上椅背,回答得兴致缺缺,“我无意和任何人维系深刻的爱恨情仇。”
“——除了你哦。”
语气一转,她声音变柔软,淋枫糖浆的棉花糖,低头用鼻尖蹭蹭他的,言行合一的亲昵。
四目相对,带各自体温的呼吸也是,路起棋一字字叫他名:“廖希。”
“你这个应激反应时不时发作一下,要不要联络我之前做咨询的老师,聊一聊天也可以,他还蛮有名的。”
“原来在惦记这个。”他手掌扶在她后脑勺,上前碰一下唇角。
路起棋过去在遥城的咨询师,廖希作为称职的男友,当然要有所了解:业内评价良好,颇具口碑。
只是这提议不太妥当,毕竟两年前逼迫这位资深敬业的心理咨询师呈文又口述,事无巨细泄露一位名为路起棋的病人档案和对话细节——简称“渎职”的要犯,如果还要上门求医,太厚颜无耻。
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这会儿振振有词:“涉及男朋友的身心健康,我超关心好不好。”
廖希想了想,干脆把她抱到腿上坐,窝在颊边咬耳朵:“其实有你就行。”
“好会见缝插针。”
他低声笑:“说真话也不让吗。”
路起棋沉默地伸手搂紧他的脖子,没再说话。
偶尔有一些时刻,她投入到某种情绪时不经意对上视线,或是醒来见廖希在枕边看自己,会露出刚刚在门边时那样的表情和眼神。
她一开始只是觉得似曾相识,仿佛很久以前在梦里见过同样的眼睛,但要回忆,又很难具体到细节,只当是他难释的愧意更多,不好她单方面说没关系的,慢慢来。
但久了就回过味来,他在眼前,像个浸湿的、永远不会干燥的伤口,路起棋没办法视若无睹。
一次两人有事分别,路起棋走出几百米远,被路口窜出的摩托车吓跌倒,一点点擦破皮和淤青,没什么大问题,只是要起身时发现t恤上的别针和牛仔裤破洞勾到一起,解开花了点时间。
很快有人上来搀她,面生但不是好心路人,开口叫她“路小姐”。站直了,隐约听见哪里传来不寻常的声响。
后面知道廖希隔一条路出车祸,是朝她这边过来的时候无视信号灯,倒霉的司机刹车不及,他右腿被撞成骨折。
路起棋事后真的蛮生气,不是玩笑打闹居多那种,检查过程里保持冷脸,对伤者更没施舍眼神和问候,转身就走。
没走出几步,身后传来噼里哐啷的动静,廖希侧身摔下来,电脑连带床头很多杂物洒落一地。
故意的,拐杖就放在床边。
“明明你叫我什么事都以自己人身安全为先。”
她还是挪腿回去,把他以前的原话也还回去。两个人都知道路起棋见弱小,迷你的胆量会膨胀一些,那时候廖希说:不是让你改了,但只有这一点,好不好。
好不好,他像央哄小孩,而不是此刻她复述的语气像风干腊肠硬邦邦。
“喝水会呛,吃饭会噎,走路会崴脚,都是日常小概率的事件,我下次屁股和手着地可能也是准备做breaking,廖希,我们要一起生活很久,放松一点,你这样——”不累吗?
路起棋居高临下地看他,眉心拧紧,没把话说尽。
她再迟钝,长期被寸步不离的安保力度环绕在周,加上枕边人紧绷的状态,藏得再好也总能察觉到一二。
他装没事人,带几分示好的意味:“宝宝,做那个容易骨折,记得戴护具。”
路起棋倒吸一口气——有人完了。
“我知道。”他突然说。
廖希半坐在地的模样好狼狈,仰头巴巴拉她的手,姿态放得低,语气像赌气又像认命。
他说:“我知道,路起棋,我没办法。”
以僵局收场,后面还是慢慢和好,他搭很多台阶过来,保证路起棋可以顺势不知不觉地走下去。
没办法,她也没办法。
人总有无解的时期和情绪。路起棋也有,被旁人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刺痛,全宇宙都惹到她。
廖希时有承载她莫名发难。
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可不可以别问。送你这朵花好不好。不好。两朵好不好。不好。不送呢。也不好。
倾向自厌自毁的瞬间也不少,男孩子的花无法消愁,男孩子的花容月貌同样无法。那时“死”字还没成为谶言晦词,路起棋事后在床上恹恹地哭完,又发狠话说一起死。
人要怎么把另一个人占为己有,她钻牛角尖到底,总不能真啖肉饮血。
如果她足够健壮聪明有权有势,以彼时的精神状态,会试图把人囚禁上演强制爱小黑屋场景也不一定。
……话说回来,假想中的受害者本人一旦知晓她这个想法,不说喜形于色,绝对跃跃欲试。
——居然是回合制!不过是回合制!
路起棋苦中作乐地想:廖希只是这个时期比较长,比较不外显,比较多多折磨他自己。
她搞不清这是否称得上是义气。路起棋心智未开化前就被教导养成习惯:幼儿园的小朋友今天送自己一支仙女棒,第二天她要带一个小汽车。
这回送的兜里塞不下,一整个书包也塞不下。衣食住行,加放在襁褓里时刻被托举抚平的情绪,花时间金钱和精力要多少,路起棋是养一棵以光合作用为生的植物都不易的人。
想起以前阿姨从国外回来,一同吃家宴时补发压岁钱,小辈里,路起棋收到尤其厚的一迭。
对大呼不公平的其他人给出解释:“棋棋跟我关系好,又是女孩。”
接着老生常谈,开展一些饭桌常驻主题,说女孩子要有富足的成长环境,长大了才不容易被外面心怀不轨油嘴滑舌的男人骗。
阿姨怅然道:“时间很快的唷。”
路起棋当时在上初中,爸爸一边接对面碰过来的杯子,一边说:“这个话题对我很残忍。”
扭头对她提醒:“到时候一定找一个像爸爸爱妈妈一样爱你的。”
妈妈翻了个白眼,“那不然呢?”
爸爸说:“…好吧,要像妈妈爱你一样爱你。”
妈妈立刻正色,用“不可能”的表情说:“这有点难。”
饭桌上的大家目光集中到一处,笃定有很多小男生给她递情书。路起棋对这个场景头大,急于转移话题,想这岂止有点难,说哦哦我们最近学到蜀道难。
心里的想法会失礼一点,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带着天然的自满优越和嫌弃:男生吗?又丑又吵又讨厌的生物。
眼前这个男人,和丑和吵和讨厌绝对搭不上关系,爱要怎么衡量相较,用刻度尺,用量筒,用天平,难于上青天是在表述难的最高级,路起棋知道他是没有她会死掉的程度。
偶尔也会反思,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动辄要死要活的琼瑶剧形态。
她在幸福浓度很高的环境里长大,不缺任一一种关爱,动心也是恰逢适宜的年纪和荷尔蒙,是样貌加性格加外在表现都合意的对象,繁重的学业间隙给足情绪。
理想健康的恋爱关系是怎样,不利于自己和对方就得终止拨正,好比那次半途而废的分手,她状态不好,也是仔细斟酌利害。
如果要给现在的生活评价,路起棋也会说“很好”。当下维持不错的人际关系,念不错的学校拿奖学金,去年底拿到结果不错的体检报告。“不错”讲起来更符合中庸之道,弹性大容错高,然而很好就是真的很好,没有什么矫饰的成分。
二者间的变量在于一个人,廖希悱恻地刺穿她温吞的壳,然后一整个变成望不到底的温柔乡。
温室里什么都养,害怕或是担忧,最适宜欲念滋长。理性无时不在敲钟,对立面的私欲嘲笑她:你不就想要这个。
想要什么,是路起棋说完一起死,廖希想也不想回“行啊”,同时伸出手臂无限耐心珍视地抱她擦眼泪。
一想到是这个人,她不由病态觉得:打不过就加入,蛮快乐的。
路起棋不会忘记给玩伴带小汽车,而从没有给收过的情书回函。因此这无关仁义礼智,不是知恩图报,是情难自禁,求仁得仁。
爱意同样可以饲喂爱,回溯最早最早的见色起意,弃之可惜的塑料袋被撑成暴食症一般不知饥饱的胃,路起棋心甘情愿地放下戒心,不是向世界和陌生人的戒心,是驱乎本能,写在基因里的疼就躲避痒就笑。
好,都可以。
她伸手用掌心盖住面前的眼睛,把自己填进一处伤口,等血肉长在一起,至少不会溃烂下去。
廖希要什么就得到,要分不开就分不开,生命各处长连在一起,肉体和灵魂彼此咬合,她这么爱胡思乱想,朝三暮四,也会认为,除了和这个人共度一生,没有第二种可能。
感知到睫毛轻轻地搔在手心,眼皮鼓起同样脆弱地抖,像一尾金鱼游,痒痒的,愈合时皮肉增生的错觉。
路起棋说:“好,不会不要你。”
她撤回手,让光掷进去,墨汪汪一面镜照出路起棋的脸,照出圆圆的杏眼弯成月,笑得很可爱地说:“没事的,我爱你,我也爱你。”
话音落下,一方空间只剩安静,室内的温度一达标,冷气就偃息,窗外的知了叫不停,芭蕉叶被烘得绿,油,皱。
并非盛典佳节,黄历上值得圈定的好日期。
路起棋说“爱”,酷似庄严的宣誓,或是交换承诺,抹平时差,无意回望一双乞怜的眼睛,梦里醒来时都见,上天入地两个人的秘密基地。
这是最平常的一个午后,天气预报显示此时气温在三十二度,遥城入夏以来的高温纪录发生在一周前,炙人惊心的三十九度,标红的数字之下,记无关紧要的一笔。
桌上西瓜还剩半碗,她同他肝胆相照。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
- 导航
- 设置
- 字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