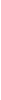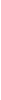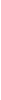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 上一章 | 目录 | 下一章 |
见太子伤得这么重,赵宝珠登时愣住。
跟太子一比,叶京华身上那点伤痕一下子就不算什么了。
赵宝珠蹙了蹙眉,瞪了眼叶京华,小声道:“你们是说了什么了?还是做了什么了?怎么把殿下气成这样?”
元治帝是最讲理的人,又一向宠爱太子和叶京华两人,打成这样,肯定是气得不轻!
叶京华闻言,动作一顿,微微站直了身。他在北镇府司关了这些时日,脸色有些白,敛着眼没说话。
赵宝珠见他这个样子又有点心疼,小声道:“待回了府再说。”
说罢,他转过头,见太子被太监搀扶着站在一旁,面若金纸的样子,终究还是担忧地上前了几步:
“……太子殿下可还好?”赵宝珠皱着眉,四处看了看:“殿下伤得这么重,怎么不见太医来?”
太子都被打成这样了,怎么一个伺候的太医都没有?现今天气凉了,若是寒气入体,落了病根那可不是小事。赵宝珠担忧得想道。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当夏内监怕太子真出了事,急急忙忙去找到元治帝时,皇帝连个人都不想派:“就让他跪着!朕看他也死不了!”
元治帝在气头上说。还是夏内监好说歹说,劝了好一会儿,元治帝才勉为其难地派了个医女过去给太子包扎。
闻言,太子的眉眼骤然柔和了些许,垂眼看向赵宝珠:“无碍,太医在东宫中候着呢。”
赵宝珠听了,这才松了口气。接着又有些尴尬,自那夜在赵府的谈话之后,这还是他头一次见到太子,赵宝珠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垂着头想了一会儿,才犹豫道:
“臣……臣还未来得及对殿下道谢。”赵宝珠抬眸看向太子:“多谢殿下愿为叶大人作保,安定群臣之心,查清了此案。”
“不必言谢,这本就是孤分内之事。”太子目光温和,道:“不如说是孤得谢你,若不是你以良言相劝,孤恐怕还糊涂着。”
闻言,赵宝珠一怔,觉得太子给人的感觉有些变了。他迎着月光,见太子目光平和,微微发白的脸上啜着温和的笑意,身上没了先前那种仿佛压抑着什么情绪的焦躁,他笑了笑,对赵宝珠道:
“让你平白忧心了一天,定是累了,快随京华回府去吧。”
赵宝珠一愣,遂也笑起来,对太子点了点头:“殿下也快回宫去吧,定要让太医好好看看伤势才是。”
太子对他笑了笑,亦点了点头,转身朝东宫的方向去了。
赵宝珠目送他离开的背影,站了小片刻,也收回目光,小跑回了叶京华身边:“少爷,咱们快回去吧。”
叶京华看了看太子离去的方向,又看了眼赵宝珠,唇角微拧,抬手牵起赵宝珠的手。
两人便朝马车走去,赵宝珠全程都跟他挨得紧紧的,将叶京华一路搀着上了马车。待将他安顿着坐好,还忧心地问:“哪里疼?”
叶京华闭着眼睛,一只手臂搭在赵宝珠肩上,闭着眼睛:“……腿疼。”过了一会儿,又小声道:“背也疼。”
“嗯?”背疼是鞭伤,腿怎么又疼了呢?赵宝珠皱着眉将叶京华衣袍的下摆拉了起来,往下头一看,就见叶京华的膝盖上有深深的两团青紫淤伤,登时一惊:“哎呀,怎么弄成这样了?”
接着转念一想,此番元治帝生了大气,必定是蒲团也不许用的,这样的大冷天在那硬石板上跪着,能不伤着吗?
赵宝珠心疼极了,将手心搓热了,按在叶京华的双膝上给他暖着:“这样可好些了?”
叶京华心都快化了。
有宝珠如此疼他,他再跪上几个时辰都不要紧。
他伸手揽住少年,在赵宝珠冻地略带凉意的脸蛋上亲了亲:“好多了,连累你在外头等我这么久。”他说着,直接将赵宝珠抱紧在了怀里,姿态极其依恋地贴着赵宝珠的乌发蹭着,低声道:“小宝,我想你了。”
男子低沉而优美的声音灌入赵宝珠耳中,一股酥麻骤然顺着脊背而上。
赵宝珠生生地打了个抖,脸颊一下就红了。在叶京华怀中低下头,说不出话来。
叶京华搂着他依偎着,过了一会儿,软声道:“小宝不想我吧”
赵宝珠哪里禁得住这个,赶忙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向叶京华:“想的……我日夜都在想少爷呢——”
闻言,叶京华笑开了,略微苍白的面上眉目粲然,双手捧住赵宝珠的脸便亲了下去。
“唔!”赵宝珠被亲了个正着,想起这还是在马车里,先是挣扎了几下,但很快就浑身酥软,被叶京华紧紧抱着,什么都不知道了。
马车外,方家兄弟坐在车辕上,裹着大袄,脸皮被北风吹得有些发麻。听着耳边北风呼啸中夹杂着的些许声响,两人对视一眼,不禁将手上握着的缰绳放松了些。
可惜太庙离叶家本府实在是不远,就算马走得再慢,也没能给小情侣留太多温存的时间。
叶府外,叶相与叶夫人夫妇俩带着一大票下人站在府门口,待马车一停,叶夫人立即抬脚迎了上去:“卿儿!”
马车停好,方氏兄弟先跳了下来,叶夫人焦急道:“人接回来了没有啊?”
方勤赶忙回道:“接回来了,二少爷和赵大人都在后头呢。”
叶夫人闻言,略略放下了心,而后又焦急地看向马车上垂下的帘子:“卿儿,快出来,让娘看看你怎么样了?”
她说完话后,又隔了片刻,帘子被一只手撩开,叶京华从马车上走了下来:“母亲。”
叶夫人赶忙上前拉住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的儿!你受苦了——”她美眸中泪光闪闪,上下打量了一番叶京华,心疼地道:“瘦了,脸色也不好看。”
“听说圣上打你了?快给娘看看伤得这么样了?”
叶夫人将叶京华的袖子拉起来一看,立即倒吸了口凉气,后退了几步,差点没翻个白眼晕过去。叶京华赶忙扶住她:“母亲不必担忧,只是些皮肉伤罢了。”
叶夫人吸了口,急道:“这怎么会没事!自从你生下来,谁动过你一根手指头——”她着急,可又不好说元治帝的不是,到底顿住了话头,叹了口气。随即注意到了什么,奇怪道:
“宝珠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叶京华闻言,神情微微一滞。还未等他开口,马车后便传来少年略微发虚的声音:“夫人,我回来了。”
叶夫人抬头看去,便见赵宝珠低着头,扭扭捏捏地从马车另一边绕了过来。叶夫人急忙伸手将他捞过来,嘴里斥道:
“你这孩子,在那黑灯瞎火的地方躲着干什么?”本来就是小小一只,藏在那犄角旮旯里头更看不见了!
赵宝珠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话,仔细看耳廓还有些红。叶夫人倒是没多心,安抚般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软声道:“好孩子,今儿真是劳烦你了,大冷天的还为了卿儿奔波。”
说罢她看了看两人,道:“快跟娘回屋去,让大夫好好看看你的伤——”
说罢就想拉着儿子儿媳往府里走,然而就在这时,站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叶执伦忽然开了口:“等等。”
叶执伦自暗处走出来,灯笼暖黄的光照在他脸上。宰相的神情有些冷,走出几步,挑剔地扫了叶京华一眼:
“怎么。”他看着叶京华,眯了眯眼,语气不阴不阳地道:“在人家的祖祠跪了,沾了光,回家就不必跪了?”
元治帝在太庙中做了什么,他一清二楚。说实话,叶执伦心里也对这两人不满许久了,只不过太子的事他不好插嘴,叶京华的事他又一向懒得管。
不过如今连太庙都跪了,若他再不出手,叶家祖宗的老脸要往哪里放?
闻言,叶京华脚步一顿,看向叶执伦。叶执伦眉梢微微一动,眸中沁出冷色:“怎么,不服?”
“不。”叶京华敛下眼,垂下头,恭敬道:“儿子犯下大错,请父亲发落。”
叶执伦紧皱的眉头这才略略松开了些,淡声道:“去后头祠堂跪着,什么时候反省了,什么时候再出来。”
闻言,叶京华还没说什么,叶夫人就先不依了:“叶执伦,你这是干什么!”
她瞪着丈夫,将儿子挡在身后:“卿儿都这样了你还让他跪?他身上有伤,还在大牢里关了那么些天,你还要罚他跪!跪坏了怎么好?那祠堂里头连个挡风的地方都没有、冻坏了怎么好?”
叶执伦蹙了蹙眉,看了眼护崽的发妻,不禁道:“他那是被关着北镇府司,算什么大牢?”
叶夫人一滞,接着更是火冒三丈:“怎么,非要卿儿下了诏狱才算得上是大牢是吧?!”
跟在后头的赵宝珠见两人要吵起来,赶忙向前走了几步,劝道:“夫人,请息怒。宰相大人说得不错,如今陛下在太庙教训了太子和殿下与少爷,这事不日就会传开,若是宰相大人没有表示,恐怕旁人或多有闲话呢。”
叶夫人闻言,面上的怒气一滞,想了想确实如此,如今元治帝带头教训了两人、显然是对叶京华有不满的,若是什么都不做,岂不是显得叶家没家教?这传出去可就太不好听了——叶夫人心中的怒气消散了些,可、可卿儿到底还是受着伤呢——
就在这时,赵宝珠又转向叶执伦:
“宰相大人,如今夜已深了,少爷刚在陛下哪儿受了罚,身上还带着伤,不如让大夫看看伤势,休息一晚再处罚吧,若真为了这个落下了病根就不好了。”
这话说得入情入理,直说到了叶夫人的心坎上。叶夫人眸光闪烁,欣慰地看向赵宝珠的背影,她这个儿媳妇儿实在是个好的!
另一边,叶执伦蹙了蹙眉,神情有些不满。然而就在这时,他的目光似是忽然注意到了什么似得微微一凝,接着神情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叶夫人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也顺着看过去。只见这会儿离府门近了些,烛光照在赵宝珠脸上,清晰可见他唇边的一点淤痕。
叶夫人见了,一愣,接着回头就狠狠瞪了叶京华一眼。这小子!怎么就这么猴急?
赵宝珠见两人忽然不说话了,还有些疑惑,接着也忽然意识到叶相和叶夫人是看到了什么,登时羞得脸通红,猛地捂住嘴低下头。
……都怪少爷!赵宝珠羞得简直想在地上刨个坑把自己埋进去。
叶夫人见状,直接伸手在叶京华手臂上拧了一下,低声斥道:“我看你劲还大得很、就该听你爹的让你好好跪一跪!”
愧得她还那么担心,还有力气折腾宝珠,她看这人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叶京华自知理亏,垂着头没吭声。叶执伦也不知该说什么,杵在灯笼旁边沉默着。叶夫人左右看了看两人,觉得这父子俩的神情很是可笑,勾了勾唇角,压下喉头的一声笑,上前打圆场道:
“行了,他们小夫妻这么久没见,也得让孩子们好好说说贴己话。”叶夫人一边说着,一边将赵宝珠和叶京华王府里推:“给大夫瞧过伤,就快些歇下——你有什么话明儿起来再说。”最后一句是朝叶执伦说的。
就这样,在叶夫人的协调下,对叶京华的处罚暂且延缓。
可也没能延缓太久,次日叶京华就被提溜去叶家祠堂跪了一天一夜。理由是次日收拾屋子的丫鬟禀报,说御赐的团花床帐被扯坏了,裂了好长的一道口子。叶执伦觉得叶京华的身子已经全好了,便直接将他扔进了祠堂里。
赵宝珠却有些愧疚——其实那床帐是他不小心弄破的,不过他也不是故意的,若不是叶京华又那样折腾他,他又顾忌着叶京华身上的鞭伤,又怎么会把床帐扯破了呢?
不过叶京华确实伤得不算重,在府里修养了几日就可以正常上朝了,而东宫那边则是许久都没有消息,对外只是说太子被皇帝禁了足,在宫内反省。
而朝廷上则是什么样的猜测都有,有人说是皇帝是不满太子意欲党政,惹了皇帝不快,也有人说皇帝是责罚太子治下不严格,也有人说是太子不满皇帝对贵妃与叶家一系宠爱太过,顶撞了皇帝,纷纷扰扰中没有定论。
众人的眼睛都盯住了皇宫——元治帝必得要就此事给群臣一个交代的,彼时或许真相便能水落石出。
霜降后,京城中的气温骤降,皇宫中已烧起了地龙。
夏内监侍候在金銮殿暖阁中,正在做上朝前的最后准备,暖阁四角燃着的暖炉噼里啪啦地响着,他拿着手中的圣旨,手都有些抖,额头不知是怕的还是热的,冒出了薄薄一层细汗。
他看着圣旨上的墨字,脚都有些发软——夏内监想到这封圣旨宣判出来时会为朝野上下带来的震动就头脑发晕。
“怎么了?”
元治帝的声音将他的神志唤回,只见皇帝姿态闲适地坐在书案后,道:“愣着干什么?”
夏内监浑身一震,随即向元治帝赔笑道:“这……奴才老了,不中用了,生怕把圣旨宣错了,得好好看看才是——”
元治帝闻言,轻笑了一声,直接点出了他的心思:“你是奇怪朕为何会如此重视赵宝珠,可是?”
夏内监哪里敢接这个话,赶忙道:“奴才不敢——”
元治帝却望向窗外,看着宫阙的红墙间飘散的细雪,继续说了下去:“忠臣的难得,但也不是没有。要说那年少聪慧、有手段的,也不止他一个。”
夏内监听到这儿,明白是皇帝自己想说,便低头敛目,不做声地在一旁听着。
“但忠顺着往往迂腐,聪慧之人不免奸滑。”
元治帝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手指在桌案上敲了敲,道:
“但这忠而不顺,慧而不奸,既有忠心,却不愚忠,敢于犯颜直谏,匡扶君主之为,才算是真正的忠臣!”
元治帝声音笃定,夏内监闻言,心头一震,将头又埋地低了些。
“皇帝虽然身负天命,但到底是凡人。凡材肉胎,孰能无过?”元治帝神情肃然,道:“朕原本是看中赵宝珠肯做实事,踏实肯干,如今一看,他远远不限于此。”
“此番瑱儿犯了糊涂,他能察君之过失且直谏,遇大变且临危不惧,亲近之人落狱,他尚且能为朝廷,为国家考虑——”
元治帝说着站了起来,双手背在身后,眸中精光大方:
“玄铁淬炼方出成色,非得经过大事才能看出人臣之资。”
听到这句话,夏内监心中大骇!元治帝可不是那种无的放矢的君主,他向来是一个唾沫一个钉子——难不成此话是在暗示赵宝珠日后将位极人臣?
他来不及惊讶,便听闻元治帝接着说下去:
“古人有言,以人为镜,方可知得失。”皇帝面上浮现出笑意,道:“赵宝珠心如明镜,朕自当委以一重用!”
此时,赵宝珠还不知道今日朝堂会有大动作,他照例站在吏部一列,探头探脑地向前头看了看,忽然发现一个高大而着赤袍的人影正站在众臣最前方。
是太子殿下!
赵宝珠登时精神一振,睁大了眼睛仔细看了看,见太子站姿挺拔,没什么不适的样子,才放下了些心来。
看来伤势是痊愈了,赵宝珠想道。
不待他多想,元治帝便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殿内,大马金刀地在龙椅上坐下。待百官跪拜之后,他一挥手便道:“今儿朕有几件要事要宣,你们先听着。”
说罢,不等百官反应,夏内监便上前一步,清了清嗓子后,朗声道:“奉天承运,皇帝召曰——”
“皇太子李瑱行事不谨,御下不严,以致衷臣受诬,朝野不宁,着夺其太子宝印,派其驻北宣府,领虎符,改革军制,以观后效。”
夏内监方宣出第一条,朝堂上就已响起清晰可闻的抽气声!
夺太子宝印!
这可是以往在废太子诏书中才会出现的话!众臣中,特别是那些坚定的储君一党,在听到前半句的时候都差点一个气上不来,然而后面半句又让他们怔住了——夺印,但赐虎符?
这不是逼着太子殿下造反吗?!
对皇家不了解的大臣此时心中纷纷发出呐喊。
但那些稍略了解圣心的老臣,在听闻皇帝夺了太子宝印却没有废太子之位时,便知道元治帝这么做约莫是想历练太子。如今的太子,也是皇三子李瑱幼年丧母,母亲又是元治帝的发妻曹氏,可以算是元治帝亲手从小带大的!这份殊荣就算是如今圣宠正隆的宸贵妃之子五皇子也没有。因此这对天家父子之间的信任关系远不是他朝可比。
果然,重臣惊讶之后立即望向队伍最前方的太子,见他神情沉静,一丝惊讶也无,显然是事先就知情的。
上方,元治帝俯瞰群臣,勾了勾嘴角——这回他发落了一帮武官勋贵,他知道那些老家伙会不满,太子自己做的蠢事,就让他自己去收拾那些烂摊子吧!
不等众臣从这道政令的震惊中平复下来,夏内监便接着宣道:
“户部侍郎叶京华,与北直隶一代施行新税律颇有成效,加巡官衔,命其驻江南以施新税律,惠及民生,检察赋税,充盈国库。”夏内监声音洪亮道:“皇帝念其归京不久,命年节休*沐后再往!”
这一项不如前面那项令群臣震惊,只有赵宝珠呼吸一滞,瞪大了眼睛看向叶京华——少爷要外放去江南了?
然而还不等他转过脑筋,夏内监的声音再次响起:
“吏部员外郎赵宝珠,清廉正直,宣德明恩,才智出众,忠诚敢谏——”夏内监洋洋洒洒地念出十数句对赵宝珠的赞美,而后道:“擢升为江南按察使,掌个州府司法刑狱,财富民生,考核官员,劝课农桑,望尔矜矜业业,不负皇恩。亦于年节休沐后赴任,钦此——”
至此,夏内监终于宣完圣旨,垂头后退一步。
赵宝珠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自己,微微长大了嘴,有好几息脑子都是空白的。而后,他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这似乎是正三品的官儿啊?
而同时,群臣中已经压抑不住议论之声,众人都跟见了鬼似得看向赵宝珠——按察使是什么官?那可是除巡抚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方大员!还是江南这等富庶之地!掌管诸事,几乎将除开军政以外的所有大权都握在手里,地方所有官员都可以被其调令!
换个角度说,方才被加了巡官衔要赴任江南的叶京华,在地方时,名义上也得受赵宝珠挟制!
众臣已经震惊地发不出声,看着亦满脸惊讶的赵宝珠如同看着一个天外来客——
一个没有背景,非世家出身,科举堪堪三甲的贫民之子,竟然就在未及弱冠之龄成了正三品的按察使?
这是何等的晋升速度!何等的皇恩!
赵宝珠在众人关注的中心发着愣,丝毫没有注意到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到了自己身上。
“宝珠。”
这时,叶京华的声音响起。赵宝珠这才猛然醒过神,对上了男子温润带着笑意的双眼。这才发觉除却他,太子与叶京华已然站出了朝臣之列。赵宝珠浑身一震,赶忙追了上去。
此刻,还是夏内监清了清嗓子,道:“请诸位接旨。“
太子,叶、赵三人便齐齐下跪,磕头谢恩:“儿臣/微臣领旨——”
“好,好,你们都是好的。以后要好好办差事,知道了吗?”元治帝如同一个慈祥的长辈般笑眯眯地叫了他们起来,而后向龙椅后靠了靠,抬眸看向面色各异的众臣:“朕要说的就是这些,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群臣间鸦雀无声——出了这么大的变动!他们还能有什么话说?!只想元治帝赶快将他们放了,让他们好好去打听打听来龙去脉——
元治帝似是也知道他们的心思,双手在龙椅上一拍,站起来道:“好,既然无事,那就散朝!”
随后便大步走出了金銮殿。皇帝一走,朝堂中的众臣登时如同渐了水的油锅般炸了开来!众人齐齐转过身,不约而同地瞪视向赵宝珠,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始说话。
“赵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下官从属吏部,赵大人,我们见过——”
“赵大人,下官乃江南出身,大人想知道什么可以问我——”
赵宝珠耳边嗡得一声,这才发现所有人都在看他,登时吓了一大跳,讶然地看向朝他不断逼近的群臣,不禁后退了一步。
这时,叶京华清冽的声音忽然穿过了他耳边嗡嗡的人声,在赵宝珠耳边炸响:
“宝珠,快走!”
赵宝珠一震,目光越过群臣对上叶京华灿若星辰的双眸,他神情急切,眼中却含着笑意:“快跑啊!”
赵宝珠怔愣了一瞬,接着猛地转过身,拔足狂奔!
“诶、诶——赵大人——”
嘈杂的人声被他甩在身后,赵宝珠像一阵风般跑出金銮殿,只留身后的群臣错愕地瞪着眼睛——还有这一招?!
赵宝珠在青石阶上奔跑,穿过层层宫峦,看着赤红色的宫墙快速地往后退去。旁边儿经过的宫人见这么个穿着官服的大人竟然在奔跑,都纷纷震惊地让开道路,目送赵宝珠越跑越远。
赵宝很擅长奔跑,毕竟在益州的深山之中,幼童之间互相追逐就是孩子们唯一的娱乐。
他跑得极快,踩过地上冷硬的石板,听到胸膛中略微急促的呼吸声,感受着脸庞边呼啸而过的冷风,不知不觉就跑出去很远。
待终于停下来之时,赵宝珠才发觉他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宫墙边儿,面前便是一道宫门。
往宫门外望去,远远便能望见街上熙熙攘攘的小贩,窗外飘着各式彩旗横幅的酒楼,喧闹繁华的集市——这正是他初入京城时走上的那条大道。
赵宝珠不禁有些怔忪。
初到京城时,他只管低着头找路,只觉得街上人潮蹿腾,将他裹挟其中,磕磕绊绊地往地上绊。彼时他只能看见街面上那比他们县城都要整齐的青石板,和京城人脚上干净又好看的布鞋,连不远处就是皇城也没看见。
而如今他站在位于高出的宫门前,他不仅能看到人,还能看到天,那些曾让他惊慌不安的人群显得分外渺小。京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皆是民生。
赵宝珠疏出一口气,想起方才朝堂上的种种,胸口骤然涌上热意,双眼明亮,抬脚迈入了光明之中——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无论是陛下,还是太子,亦或是叶京华,都是他三生有幸才得以相遇的’好风‘。而这青云之志,也得惠及万民,方不算辜负了上天对他的眷顾。
赵宝珠向宫门外迈去,踌躇满志,心中再无阴云。
全文完
跟太子一比,叶京华身上那点伤痕一下子就不算什么了。
赵宝珠蹙了蹙眉,瞪了眼叶京华,小声道:“你们是说了什么了?还是做了什么了?怎么把殿下气成这样?”
元治帝是最讲理的人,又一向宠爱太子和叶京华两人,打成这样,肯定是气得不轻!
叶京华闻言,动作一顿,微微站直了身。他在北镇府司关了这些时日,脸色有些白,敛着眼没说话。
赵宝珠见他这个样子又有点心疼,小声道:“待回了府再说。”
说罢,他转过头,见太子被太监搀扶着站在一旁,面若金纸的样子,终究还是担忧地上前了几步:
“……太子殿下可还好?”赵宝珠皱着眉,四处看了看:“殿下伤得这么重,怎么不见太医来?”
太子都被打成这样了,怎么一个伺候的太医都没有?现今天气凉了,若是寒气入体,落了病根那可不是小事。赵宝珠担忧得想道。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当夏内监怕太子真出了事,急急忙忙去找到元治帝时,皇帝连个人都不想派:“就让他跪着!朕看他也死不了!”
元治帝在气头上说。还是夏内监好说歹说,劝了好一会儿,元治帝才勉为其难地派了个医女过去给太子包扎。
闻言,太子的眉眼骤然柔和了些许,垂眼看向赵宝珠:“无碍,太医在东宫中候着呢。”
赵宝珠听了,这才松了口气。接着又有些尴尬,自那夜在赵府的谈话之后,这还是他头一次见到太子,赵宝珠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垂着头想了一会儿,才犹豫道:
“臣……臣还未来得及对殿下道谢。”赵宝珠抬眸看向太子:“多谢殿下愿为叶大人作保,安定群臣之心,查清了此案。”
“不必言谢,这本就是孤分内之事。”太子目光温和,道:“不如说是孤得谢你,若不是你以良言相劝,孤恐怕还糊涂着。”
闻言,赵宝珠一怔,觉得太子给人的感觉有些变了。他迎着月光,见太子目光平和,微微发白的脸上啜着温和的笑意,身上没了先前那种仿佛压抑着什么情绪的焦躁,他笑了笑,对赵宝珠道:
“让你平白忧心了一天,定是累了,快随京华回府去吧。”
赵宝珠一愣,遂也笑起来,对太子点了点头:“殿下也快回宫去吧,定要让太医好好看看伤势才是。”
太子对他笑了笑,亦点了点头,转身朝东宫的方向去了。
赵宝珠目送他离开的背影,站了小片刻,也收回目光,小跑回了叶京华身边:“少爷,咱们快回去吧。”
叶京华看了看太子离去的方向,又看了眼赵宝珠,唇角微拧,抬手牵起赵宝珠的手。
两人便朝马车走去,赵宝珠全程都跟他挨得紧紧的,将叶京华一路搀着上了马车。待将他安顿着坐好,还忧心地问:“哪里疼?”
叶京华闭着眼睛,一只手臂搭在赵宝珠肩上,闭着眼睛:“……腿疼。”过了一会儿,又小声道:“背也疼。”
“嗯?”背疼是鞭伤,腿怎么又疼了呢?赵宝珠皱着眉将叶京华衣袍的下摆拉了起来,往下头一看,就见叶京华的膝盖上有深深的两团青紫淤伤,登时一惊:“哎呀,怎么弄成这样了?”
接着转念一想,此番元治帝生了大气,必定是蒲团也不许用的,这样的大冷天在那硬石板上跪着,能不伤着吗?
赵宝珠心疼极了,将手心搓热了,按在叶京华的双膝上给他暖着:“这样可好些了?”
叶京华心都快化了。
有宝珠如此疼他,他再跪上几个时辰都不要紧。
他伸手揽住少年,在赵宝珠冻地略带凉意的脸蛋上亲了亲:“好多了,连累你在外头等我这么久。”他说着,直接将赵宝珠抱紧在了怀里,姿态极其依恋地贴着赵宝珠的乌发蹭着,低声道:“小宝,我想你了。”
男子低沉而优美的声音灌入赵宝珠耳中,一股酥麻骤然顺着脊背而上。
赵宝珠生生地打了个抖,脸颊一下就红了。在叶京华怀中低下头,说不出话来。
叶京华搂着他依偎着,过了一会儿,软声道:“小宝不想我吧”
赵宝珠哪里禁得住这个,赶忙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向叶京华:“想的……我日夜都在想少爷呢——”
闻言,叶京华笑开了,略微苍白的面上眉目粲然,双手捧住赵宝珠的脸便亲了下去。
“唔!”赵宝珠被亲了个正着,想起这还是在马车里,先是挣扎了几下,但很快就浑身酥软,被叶京华紧紧抱着,什么都不知道了。
马车外,方家兄弟坐在车辕上,裹着大袄,脸皮被北风吹得有些发麻。听着耳边北风呼啸中夹杂着的些许声响,两人对视一眼,不禁将手上握着的缰绳放松了些。
可惜太庙离叶家本府实在是不远,就算马走得再慢,也没能给小情侣留太多温存的时间。
叶府外,叶相与叶夫人夫妇俩带着一大票下人站在府门口,待马车一停,叶夫人立即抬脚迎了上去:“卿儿!”
马车停好,方氏兄弟先跳了下来,叶夫人焦急道:“人接回来了没有啊?”
方勤赶忙回道:“接回来了,二少爷和赵大人都在后头呢。”
叶夫人闻言,略略放下了心,而后又焦急地看向马车上垂下的帘子:“卿儿,快出来,让娘看看你怎么样了?”
她说完话后,又隔了片刻,帘子被一只手撩开,叶京华从马车上走了下来:“母亲。”
叶夫人赶忙上前拉住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的儿!你受苦了——”她美眸中泪光闪闪,上下打量了一番叶京华,心疼地道:“瘦了,脸色也不好看。”
“听说圣上打你了?快给娘看看伤得这么样了?”
叶夫人将叶京华的袖子拉起来一看,立即倒吸了口凉气,后退了几步,差点没翻个白眼晕过去。叶京华赶忙扶住她:“母亲不必担忧,只是些皮肉伤罢了。”
叶夫人吸了口,急道:“这怎么会没事!自从你生下来,谁动过你一根手指头——”她着急,可又不好说元治帝的不是,到底顿住了话头,叹了口气。随即注意到了什么,奇怪道:
“宝珠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叶京华闻言,神情微微一滞。还未等他开口,马车后便传来少年略微发虚的声音:“夫人,我回来了。”
叶夫人抬头看去,便见赵宝珠低着头,扭扭捏捏地从马车另一边绕了过来。叶夫人急忙伸手将他捞过来,嘴里斥道:
“你这孩子,在那黑灯瞎火的地方躲着干什么?”本来就是小小一只,藏在那犄角旮旯里头更看不见了!
赵宝珠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话,仔细看耳廓还有些红。叶夫人倒是没多心,安抚般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软声道:“好孩子,今儿真是劳烦你了,大冷天的还为了卿儿奔波。”
说罢她看了看两人,道:“快跟娘回屋去,让大夫好好看看你的伤——”
说罢就想拉着儿子儿媳往府里走,然而就在这时,站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叶执伦忽然开了口:“等等。”
叶执伦自暗处走出来,灯笼暖黄的光照在他脸上。宰相的神情有些冷,走出几步,挑剔地扫了叶京华一眼:
“怎么。”他看着叶京华,眯了眯眼,语气不阴不阳地道:“在人家的祖祠跪了,沾了光,回家就不必跪了?”
元治帝在太庙中做了什么,他一清二楚。说实话,叶执伦心里也对这两人不满许久了,只不过太子的事他不好插嘴,叶京华的事他又一向懒得管。
不过如今连太庙都跪了,若他再不出手,叶家祖宗的老脸要往哪里放?
闻言,叶京华脚步一顿,看向叶执伦。叶执伦眉梢微微一动,眸中沁出冷色:“怎么,不服?”
“不。”叶京华敛下眼,垂下头,恭敬道:“儿子犯下大错,请父亲发落。”
叶执伦紧皱的眉头这才略略松开了些,淡声道:“去后头祠堂跪着,什么时候反省了,什么时候再出来。”
闻言,叶京华还没说什么,叶夫人就先不依了:“叶执伦,你这是干什么!”
她瞪着丈夫,将儿子挡在身后:“卿儿都这样了你还让他跪?他身上有伤,还在大牢里关了那么些天,你还要罚他跪!跪坏了怎么好?那祠堂里头连个挡风的地方都没有、冻坏了怎么好?”
叶执伦蹙了蹙眉,看了眼护崽的发妻,不禁道:“他那是被关着北镇府司,算什么大牢?”
叶夫人一滞,接着更是火冒三丈:“怎么,非要卿儿下了诏狱才算得上是大牢是吧?!”
跟在后头的赵宝珠见两人要吵起来,赶忙向前走了几步,劝道:“夫人,请息怒。宰相大人说得不错,如今陛下在太庙教训了太子和殿下与少爷,这事不日就会传开,若是宰相大人没有表示,恐怕旁人或多有闲话呢。”
叶夫人闻言,面上的怒气一滞,想了想确实如此,如今元治帝带头教训了两人、显然是对叶京华有不满的,若是什么都不做,岂不是显得叶家没家教?这传出去可就太不好听了——叶夫人心中的怒气消散了些,可、可卿儿到底还是受着伤呢——
就在这时,赵宝珠又转向叶执伦:
“宰相大人,如今夜已深了,少爷刚在陛下哪儿受了罚,身上还带着伤,不如让大夫看看伤势,休息一晚再处罚吧,若真为了这个落下了病根就不好了。”
这话说得入情入理,直说到了叶夫人的心坎上。叶夫人眸光闪烁,欣慰地看向赵宝珠的背影,她这个儿媳妇儿实在是个好的!
另一边,叶执伦蹙了蹙眉,神情有些不满。然而就在这时,他的目光似是忽然注意到了什么似得微微一凝,接着神情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叶夫人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也顺着看过去。只见这会儿离府门近了些,烛光照在赵宝珠脸上,清晰可见他唇边的一点淤痕。
叶夫人见了,一愣,接着回头就狠狠瞪了叶京华一眼。这小子!怎么就这么猴急?
赵宝珠见两人忽然不说话了,还有些疑惑,接着也忽然意识到叶相和叶夫人是看到了什么,登时羞得脸通红,猛地捂住嘴低下头。
……都怪少爷!赵宝珠羞得简直想在地上刨个坑把自己埋进去。
叶夫人见状,直接伸手在叶京华手臂上拧了一下,低声斥道:“我看你劲还大得很、就该听你爹的让你好好跪一跪!”
愧得她还那么担心,还有力气折腾宝珠,她看这人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叶京华自知理亏,垂着头没吭声。叶执伦也不知该说什么,杵在灯笼旁边沉默着。叶夫人左右看了看两人,觉得这父子俩的神情很是可笑,勾了勾唇角,压下喉头的一声笑,上前打圆场道:
“行了,他们小夫妻这么久没见,也得让孩子们好好说说贴己话。”叶夫人一边说着,一边将赵宝珠和叶京华王府里推:“给大夫瞧过伤,就快些歇下——你有什么话明儿起来再说。”最后一句是朝叶执伦说的。
就这样,在叶夫人的协调下,对叶京华的处罚暂且延缓。
可也没能延缓太久,次日叶京华就被提溜去叶家祠堂跪了一天一夜。理由是次日收拾屋子的丫鬟禀报,说御赐的团花床帐被扯坏了,裂了好长的一道口子。叶执伦觉得叶京华的身子已经全好了,便直接将他扔进了祠堂里。
赵宝珠却有些愧疚——其实那床帐是他不小心弄破的,不过他也不是故意的,若不是叶京华又那样折腾他,他又顾忌着叶京华身上的鞭伤,又怎么会把床帐扯破了呢?
不过叶京华确实伤得不算重,在府里修养了几日就可以正常上朝了,而东宫那边则是许久都没有消息,对外只是说太子被皇帝禁了足,在宫内反省。
而朝廷上则是什么样的猜测都有,有人说是皇帝是不满太子意欲党政,惹了皇帝不快,也有人说皇帝是责罚太子治下不严格,也有人说是太子不满皇帝对贵妃与叶家一系宠爱太过,顶撞了皇帝,纷纷扰扰中没有定论。
众人的眼睛都盯住了皇宫——元治帝必得要就此事给群臣一个交代的,彼时或许真相便能水落石出。
霜降后,京城中的气温骤降,皇宫中已烧起了地龙。
夏内监侍候在金銮殿暖阁中,正在做上朝前的最后准备,暖阁四角燃着的暖炉噼里啪啦地响着,他拿着手中的圣旨,手都有些抖,额头不知是怕的还是热的,冒出了薄薄一层细汗。
他看着圣旨上的墨字,脚都有些发软——夏内监想到这封圣旨宣判出来时会为朝野上下带来的震动就头脑发晕。
“怎么了?”
元治帝的声音将他的神志唤回,只见皇帝姿态闲适地坐在书案后,道:“愣着干什么?”
夏内监浑身一震,随即向元治帝赔笑道:“这……奴才老了,不中用了,生怕把圣旨宣错了,得好好看看才是——”
元治帝闻言,轻笑了一声,直接点出了他的心思:“你是奇怪朕为何会如此重视赵宝珠,可是?”
夏内监哪里敢接这个话,赶忙道:“奴才不敢——”
元治帝却望向窗外,看着宫阙的红墙间飘散的细雪,继续说了下去:“忠臣的难得,但也不是没有。要说那年少聪慧、有手段的,也不止他一个。”
夏内监听到这儿,明白是皇帝自己想说,便低头敛目,不做声地在一旁听着。
“但忠顺着往往迂腐,聪慧之人不免奸滑。”
元治帝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手指在桌案上敲了敲,道:
“但这忠而不顺,慧而不奸,既有忠心,却不愚忠,敢于犯颜直谏,匡扶君主之为,才算是真正的忠臣!”
元治帝声音笃定,夏内监闻言,心头一震,将头又埋地低了些。
“皇帝虽然身负天命,但到底是凡人。凡材肉胎,孰能无过?”元治帝神情肃然,道:“朕原本是看中赵宝珠肯做实事,踏实肯干,如今一看,他远远不限于此。”
“此番瑱儿犯了糊涂,他能察君之过失且直谏,遇大变且临危不惧,亲近之人落狱,他尚且能为朝廷,为国家考虑——”
元治帝说着站了起来,双手背在身后,眸中精光大方:
“玄铁淬炼方出成色,非得经过大事才能看出人臣之资。”
听到这句话,夏内监心中大骇!元治帝可不是那种无的放矢的君主,他向来是一个唾沫一个钉子——难不成此话是在暗示赵宝珠日后将位极人臣?
他来不及惊讶,便听闻元治帝接着说下去:
“古人有言,以人为镜,方可知得失。”皇帝面上浮现出笑意,道:“赵宝珠心如明镜,朕自当委以一重用!”
此时,赵宝珠还不知道今日朝堂会有大动作,他照例站在吏部一列,探头探脑地向前头看了看,忽然发现一个高大而着赤袍的人影正站在众臣最前方。
是太子殿下!
赵宝珠登时精神一振,睁大了眼睛仔细看了看,见太子站姿挺拔,没什么不适的样子,才放下了些心来。
看来伤势是痊愈了,赵宝珠想道。
不待他多想,元治帝便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殿内,大马金刀地在龙椅上坐下。待百官跪拜之后,他一挥手便道:“今儿朕有几件要事要宣,你们先听着。”
说罢,不等百官反应,夏内监便上前一步,清了清嗓子后,朗声道:“奉天承运,皇帝召曰——”
“皇太子李瑱行事不谨,御下不严,以致衷臣受诬,朝野不宁,着夺其太子宝印,派其驻北宣府,领虎符,改革军制,以观后效。”
夏内监方宣出第一条,朝堂上就已响起清晰可闻的抽气声!
夺太子宝印!
这可是以往在废太子诏书中才会出现的话!众臣中,特别是那些坚定的储君一党,在听到前半句的时候都差点一个气上不来,然而后面半句又让他们怔住了——夺印,但赐虎符?
这不是逼着太子殿下造反吗?!
对皇家不了解的大臣此时心中纷纷发出呐喊。
但那些稍略了解圣心的老臣,在听闻皇帝夺了太子宝印却没有废太子之位时,便知道元治帝这么做约莫是想历练太子。如今的太子,也是皇三子李瑱幼年丧母,母亲又是元治帝的发妻曹氏,可以算是元治帝亲手从小带大的!这份殊荣就算是如今圣宠正隆的宸贵妃之子五皇子也没有。因此这对天家父子之间的信任关系远不是他朝可比。
果然,重臣惊讶之后立即望向队伍最前方的太子,见他神情沉静,一丝惊讶也无,显然是事先就知情的。
上方,元治帝俯瞰群臣,勾了勾嘴角——这回他发落了一帮武官勋贵,他知道那些老家伙会不满,太子自己做的蠢事,就让他自己去收拾那些烂摊子吧!
不等众臣从这道政令的震惊中平复下来,夏内监便接着宣道:
“户部侍郎叶京华,与北直隶一代施行新税律颇有成效,加巡官衔,命其驻江南以施新税律,惠及民生,检察赋税,充盈国库。”夏内监声音洪亮道:“皇帝念其归京不久,命年节休*沐后再往!”
这一项不如前面那项令群臣震惊,只有赵宝珠呼吸一滞,瞪大了眼睛看向叶京华——少爷要外放去江南了?
然而还不等他转过脑筋,夏内监的声音再次响起:
“吏部员外郎赵宝珠,清廉正直,宣德明恩,才智出众,忠诚敢谏——”夏内监洋洋洒洒地念出十数句对赵宝珠的赞美,而后道:“擢升为江南按察使,掌个州府司法刑狱,财富民生,考核官员,劝课农桑,望尔矜矜业业,不负皇恩。亦于年节休沐后赴任,钦此——”
至此,夏内监终于宣完圣旨,垂头后退一步。
赵宝珠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自己,微微长大了嘴,有好几息脑子都是空白的。而后,他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这似乎是正三品的官儿啊?
而同时,群臣中已经压抑不住议论之声,众人都跟见了鬼似得看向赵宝珠——按察使是什么官?那可是除巡抚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方大员!还是江南这等富庶之地!掌管诸事,几乎将除开军政以外的所有大权都握在手里,地方所有官员都可以被其调令!
换个角度说,方才被加了巡官衔要赴任江南的叶京华,在地方时,名义上也得受赵宝珠挟制!
众臣已经震惊地发不出声,看着亦满脸惊讶的赵宝珠如同看着一个天外来客——
一个没有背景,非世家出身,科举堪堪三甲的贫民之子,竟然就在未及弱冠之龄成了正三品的按察使?
这是何等的晋升速度!何等的皇恩!
赵宝珠在众人关注的中心发着愣,丝毫没有注意到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到了自己身上。
“宝珠。”
这时,叶京华的声音响起。赵宝珠这才猛然醒过神,对上了男子温润带着笑意的双眼。这才发觉除却他,太子与叶京华已然站出了朝臣之列。赵宝珠浑身一震,赶忙追了上去。
此刻,还是夏内监清了清嗓子,道:“请诸位接旨。“
太子,叶、赵三人便齐齐下跪,磕头谢恩:“儿臣/微臣领旨——”
“好,好,你们都是好的。以后要好好办差事,知道了吗?”元治帝如同一个慈祥的长辈般笑眯眯地叫了他们起来,而后向龙椅后靠了靠,抬眸看向面色各异的众臣:“朕要说的就是这些,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群臣间鸦雀无声——出了这么大的变动!他们还能有什么话说?!只想元治帝赶快将他们放了,让他们好好去打听打听来龙去脉——
元治帝似是也知道他们的心思,双手在龙椅上一拍,站起来道:“好,既然无事,那就散朝!”
随后便大步走出了金銮殿。皇帝一走,朝堂中的众臣登时如同渐了水的油锅般炸了开来!众人齐齐转过身,不约而同地瞪视向赵宝珠,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始说话。
“赵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下官从属吏部,赵大人,我们见过——”
“赵大人,下官乃江南出身,大人想知道什么可以问我——”
赵宝珠耳边嗡得一声,这才发现所有人都在看他,登时吓了一大跳,讶然地看向朝他不断逼近的群臣,不禁后退了一步。
这时,叶京华清冽的声音忽然穿过了他耳边嗡嗡的人声,在赵宝珠耳边炸响:
“宝珠,快走!”
赵宝珠一震,目光越过群臣对上叶京华灿若星辰的双眸,他神情急切,眼中却含着笑意:“快跑啊!”
赵宝珠怔愣了一瞬,接着猛地转过身,拔足狂奔!
“诶、诶——赵大人——”
嘈杂的人声被他甩在身后,赵宝珠像一阵风般跑出金銮殿,只留身后的群臣错愕地瞪着眼睛——还有这一招?!
赵宝珠在青石阶上奔跑,穿过层层宫峦,看着赤红色的宫墙快速地往后退去。旁边儿经过的宫人见这么个穿着官服的大人竟然在奔跑,都纷纷震惊地让开道路,目送赵宝珠越跑越远。
赵宝很擅长奔跑,毕竟在益州的深山之中,幼童之间互相追逐就是孩子们唯一的娱乐。
他跑得极快,踩过地上冷硬的石板,听到胸膛中略微急促的呼吸声,感受着脸庞边呼啸而过的冷风,不知不觉就跑出去很远。
待终于停下来之时,赵宝珠才发觉他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宫墙边儿,面前便是一道宫门。
往宫门外望去,远远便能望见街上熙熙攘攘的小贩,窗外飘着各式彩旗横幅的酒楼,喧闹繁华的集市——这正是他初入京城时走上的那条大道。
赵宝珠不禁有些怔忪。
初到京城时,他只管低着头找路,只觉得街上人潮蹿腾,将他裹挟其中,磕磕绊绊地往地上绊。彼时他只能看见街面上那比他们县城都要整齐的青石板,和京城人脚上干净又好看的布鞋,连不远处就是皇城也没看见。
而如今他站在位于高出的宫门前,他不仅能看到人,还能看到天,那些曾让他惊慌不安的人群显得分外渺小。京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皆是民生。
赵宝珠疏出一口气,想起方才朝堂上的种种,胸口骤然涌上热意,双眼明亮,抬脚迈入了光明之中——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无论是陛下,还是太子,亦或是叶京华,都是他三生有幸才得以相遇的’好风‘。而这青云之志,也得惠及万民,方不算辜负了上天对他的眷顾。
赵宝珠向宫门外迈去,踌躇满志,心中再无阴云。
全文完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
- 导航
- 设置
- 字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