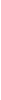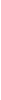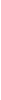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 上一章 | 目录 | 下一章 |
“……前几日屋顶漏雨,找来人修了修,觉得这铺子也有些年头,放药窄得很,想搭钱再往旁边扩扩。你回来得正好,替我瞧瞧扩多大合适?”
“……老苗?老苗如今不得了,他长得老,怪会唬人的,说实话,来找他瞧诊的人比你当初在的时候还多。可见老树皮也能有再一春。”
“银筝就不提了,吃我的住我的,脾气还大,说两句还常不乐意,要不是你的人,我早就好好教训她一番,教她知道什么叫尊重东家。”
“……阿城过了年也不小了,银筝平日里教他识字什么的,我估摸着要不行也学吴秀才,让他上上学堂,万一考中了,我就能多个当官的儿子孝敬,享享清福……”
“反正一切照旧,发不了财也饿不死,你要是在医官院干不下去了还能回来。看在咱俩以前的交情上,东家施舍你个坐馆大夫当当……”
他絮絮叨叨说了许多。
其间夹杂着阿城的打断和苗良方的反驳,抑或银筝的讽刺,略显嘈杂,却又如这四月春日里照在人头顶的日头,暖洋洋晒得人安心。
这顿饭吃得很长。
杜长卿又是第一个醉倒的。
阿城扶着大少爷提前回家去了,免得又如新年时分般吐得满地都是。苗良方倒是还想和陆曈多说几句,奈何前面铺子有人来瞧诊,耽误不得,便也只能先去瞧病人——没了杏林堂,西街独一家的医馆就显得珍贵起来。
陆曈和银筝把院子里的残羹剩炙收拾干净,又坐着歇息片刻,日头渐渐西沉,医馆门口的李子树被晚风吹得“唰啦啦”作响,霞色斜斜照过房瓦,铺满整个小院。
夜快降临了。
银筝陪着陆曈在院子里坐了会儿,直到前面苗良方进来催促,说天色晚了要关门,让银筝去前头清点今天剩下的药材,银筝才先出去。
院子里便只剩下陆曈一个人。
霞光晚照,日头落下,渐渐光线暗了下去,天却隐隐亮了起来,银蓝长空上出现个浅浅弯月,薄薄的挂在梢头,随着天边的浮云聚散微明微暗。
陆曈低着眼坐着。
她在医官院呆了几个月,每日给人行诊、做药,采红芳絮也好,给金显荣施针也好,内心总是无波无澜,似汪死水。
然而一进仁心医馆,便如这死水也得了一丝生机,那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宁静,仿佛风筝在漫无天际的长空与人间得了一丝细细的线,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彼此牵连。
身后传来响动声。
银筝挑开毡帘,外头的风便顺着帘子穿来一隙。她走到院中梅树下,将挂在梢头那盏红纱提灯点亮,小院就有了点金红色的光。
苗良方跟在她身后:“小陆。”
他踟蹰着,扶着拐棍的手紧了又松,银筝看看陆曈,又看看苗良方,倏地一笑:“厨房里还有些药材,我先过去收拾一下,省得夜里被老鼠抓了。”
话毕,自己端着盏油灯走了。
苗良方松了口气,拄着拐棍一瘸一拐走到石桌前,在陆曈对面坐下来。
“苗先生。”
陆曈望向苗良方。
苗良方看上去和过去有些不同。
她走时苗良方尚未在医馆正式坐馆,虽杜长卿说了要他在医馆里行诊,苗良方虽是激动,瞧着却不乏忐忑。几月未见,他胡子留长了些,洗得干干净净,修剪成山羊须形状。穿件阔袖宽大褐色麻衣,麻布束起发髻,不见从前佝偻,多了几分疏旷。
的确像位经验丰富、性情分明的老大夫。
陆曈便笑了笑:“苗先生瞧着近来不错。”
苗良方也跟着笑,有些感慨:“是挺好。”
当年被赶出医官院,他多年不曾也不敢行医,未曾想到有生之年还有为人施诊的机会。西街街邻不知他往事,他在杜长卿的医馆里为人行诊,有时候来瞧病的病人贫苦,他便不收诊银,杜长卿见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令人唏嘘的是,多年以前他一心想通过春试进入翰林医官院,偏偏在如今潦倒一无所有之时,方才得行祖上多年之教诲——
“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尤见其仁且廉也。”
世事弄人。
收回思绪,苗良方看向陆曈,神色有些担忧:“小陆你呢……进了医官院后,可有被人为难?”
平人医工初进医官院,会受到什么样的区别待遇,苗良方比谁都清楚。当年的他亦有不平之心,何况陆曈这样年轻娇弱的姑娘。
“没有。”陆曈摇头,“医官院一切顺遂,并无她事发生。”沉默了一下她才继续说道:“只是答应苗先生的事,现下还无法兑现,初入医官院,行事不好冒险。”
她说的是对付崔岷一事。
闻言,苗良方连连摆手,急道:“我就是想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做此事太过危险,当初之事、《苗氏良方》……都不强求了。”
或许人安逸日子过得好了,便会感谢上天垂怜,对于“仇恨”与“不甘”也会冲淡许多。如今在仁心医馆寻到安定,对于往事也释怀几分。他想,崔岷虽然夺走《苗氏良方》改成《崔氏药理》,可说到底,那药方传给天下医者,也是造福百姓。
此恩通天地,便不必计较芳垂万世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而陆曈,也不必为他一己之私断送大好前程。
陆曈默然。
过了一会儿,她才慢慢开口:“答应先生一事,我一定会做到,这是当初你我做好交易的条件。”
“小陆……”
“其实我今日回来,还有一事想请教苗先生。”陆曈打断他的话。
苗良方一愣:“何事?”
整个西街陷入沉沉夜色,风从更高处刮来,把梅树上挂着的红纱灯笼吹得摇摇晃晃,拉扯着地上凌乱的树影。
陆曈收回视线。
她道:“苗先生当年在医官院做院使多年,医官院医库中各官户记录在册的医案应当都已看过。”
“我想问苗先生,当今太师戚清府上嫡出公子戚玉台……”
“过去曾有视误妄见、知觉错乱之症吗?”
苗良方怔住。
四周阒然无声。
第一百五十五章 登门裴府
淡月藏在屋檐下露出半头,夜风穿过梅树枝隙,把晒在窗前的医籍吹得窸窣乱响。
良久,苗良方开口,望向陆曈的目光满是疑惑。
“小陆,你问这个做什么?”
陆曈沉默。
那一日医官院医库中,她见到了戚玉台的医案。
戚玉台早已及冠,医案记录之言却寥寥无几,或许是因过去多年身体康健并无大碍。然而五年前的深夜,他却请医官院院使崔岷出诊,为他行诊。
医案记载戚玉台是因肝火炽盛而郁结成积,相火内盛以致失调,崔岷所开药方也皆是些疏肝解郁、滋阴生津之材。
但陆曈却瞧见其中还有一些别的药材,多是宁心安神一类。
戚玉台这份医案写得极为简略,几乎没有任何病者情状记录,只有简单几句结果。在那之后近半年时间里,戚玉台又请崔岷为他行诊几次以固根本,但所用药材,亦是多以镇定去癫为主。
加之先前在司礼府,戚玉台自己也亲口承认,多年使用灵犀香安神。
桩桩件件,倒像是长期为稳癫症之行……
然而医案记录有限,此等秘辛又无旁人知晓,便只能回医馆向苗良方讨教。
陆曈抬眼:“苗先生,能告诉我吗?”
苗良方哽了一下。
这位年轻女医官精通各类毒物药理,身份神秘成谜,杜长卿与她相处甚久对她也几乎一无所知,还有银筝,素日里同西街一众街邻谈天说地,唯独对陆曈的事守口如瓶,不发一言。
她怀揣秘密而来,没人知道她想做什么。来到西街不到一年,扶持医馆、制售药茶、春试、进医官院,到最后临走时,还不忘安排仁心医馆各人今后各自归处。
但其实她今年也才十七岁而已。
若他自己有女儿,如今也当就是这个年纪了。
苗良方叹了口气,道:“没有。”
陆曈一怔。
“我离开医官院之前,不曾听说戚玉台有癫症臆病,抑或视误妄见、知觉错乱之症。”
他说得很肯定。
陆曈微微攥紧手心。
没有。
那些医案上的安神药材和长期使用的灵犀香……若无此症,何须长年调养?
何况她当日曾摸过戚玉台的脉,脉细而涩,是血虚神失所养,倒不像是因服用寒食散所致。
只是单看戚玉台言行举止,确实与寻常人无异。
莫非……
是她想岔了?
正想着,耳边传来苗良方的声音:“不过你这么说,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事。”
“先生请说。”
“我离开医官院时,戚玉台还是个半大孩子,他的事我不甚清楚。但是十多年前,我曾给戚玉台母亲行诊……他母亲,是有妄语谵言之症。”
陆曈猛地抬头:“什么?”
苗良方道:“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苗良方刚当上医官院院使不久。
他医术出众,颇得皇家人喜爱,又有“天才医官”的名头在身,不免有几分得意。朝中老臣大官有个头疼脑热的常常拿帖子来请他,有时候忙起来了,也不是人人都能请得动的。
有一日苗良方接了个帖子,是戚清府上的。
当年戚清还不如现在这般权倾朝野、只手遮天,戚家人来得急,只说戚夫人病重,请苗良方赶紧去瞧瞧。
苗良方便提起医箱匆匆去了戚府。
戚夫人是戚清的第二任妻子。
戚清早年间有位夫人,身体不好,早早就去了,也没留下一儿半女。戚清直到中年才娶了这房继室,是礼部尚书仲大人的小女儿,比戚清小了近二十岁。
“……老苗?老苗如今不得了,他长得老,怪会唬人的,说实话,来找他瞧诊的人比你当初在的时候还多。可见老树皮也能有再一春。”
“银筝就不提了,吃我的住我的,脾气还大,说两句还常不乐意,要不是你的人,我早就好好教训她一番,教她知道什么叫尊重东家。”
“……阿城过了年也不小了,银筝平日里教他识字什么的,我估摸着要不行也学吴秀才,让他上上学堂,万一考中了,我就能多个当官的儿子孝敬,享享清福……”
“反正一切照旧,发不了财也饿不死,你要是在医官院干不下去了还能回来。看在咱俩以前的交情上,东家施舍你个坐馆大夫当当……”
他絮絮叨叨说了许多。
其间夹杂着阿城的打断和苗良方的反驳,抑或银筝的讽刺,略显嘈杂,却又如这四月春日里照在人头顶的日头,暖洋洋晒得人安心。
这顿饭吃得很长。
杜长卿又是第一个醉倒的。
阿城扶着大少爷提前回家去了,免得又如新年时分般吐得满地都是。苗良方倒是还想和陆曈多说几句,奈何前面铺子有人来瞧诊,耽误不得,便也只能先去瞧病人——没了杏林堂,西街独一家的医馆就显得珍贵起来。
陆曈和银筝把院子里的残羹剩炙收拾干净,又坐着歇息片刻,日头渐渐西沉,医馆门口的李子树被晚风吹得“唰啦啦”作响,霞色斜斜照过房瓦,铺满整个小院。
夜快降临了。
银筝陪着陆曈在院子里坐了会儿,直到前面苗良方进来催促,说天色晚了要关门,让银筝去前头清点今天剩下的药材,银筝才先出去。
院子里便只剩下陆曈一个人。
霞光晚照,日头落下,渐渐光线暗了下去,天却隐隐亮了起来,银蓝长空上出现个浅浅弯月,薄薄的挂在梢头,随着天边的浮云聚散微明微暗。
陆曈低着眼坐着。
她在医官院呆了几个月,每日给人行诊、做药,采红芳絮也好,给金显荣施针也好,内心总是无波无澜,似汪死水。
然而一进仁心医馆,便如这死水也得了一丝生机,那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宁静,仿佛风筝在漫无天际的长空与人间得了一丝细细的线,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彼此牵连。
身后传来响动声。
银筝挑开毡帘,外头的风便顺着帘子穿来一隙。她走到院中梅树下,将挂在梢头那盏红纱提灯点亮,小院就有了点金红色的光。
苗良方跟在她身后:“小陆。”
他踟蹰着,扶着拐棍的手紧了又松,银筝看看陆曈,又看看苗良方,倏地一笑:“厨房里还有些药材,我先过去收拾一下,省得夜里被老鼠抓了。”
话毕,自己端着盏油灯走了。
苗良方松了口气,拄着拐棍一瘸一拐走到石桌前,在陆曈对面坐下来。
“苗先生。”
陆曈望向苗良方。
苗良方看上去和过去有些不同。
她走时苗良方尚未在医馆正式坐馆,虽杜长卿说了要他在医馆里行诊,苗良方虽是激动,瞧着却不乏忐忑。几月未见,他胡子留长了些,洗得干干净净,修剪成山羊须形状。穿件阔袖宽大褐色麻衣,麻布束起发髻,不见从前佝偻,多了几分疏旷。
的确像位经验丰富、性情分明的老大夫。
陆曈便笑了笑:“苗先生瞧着近来不错。”
苗良方也跟着笑,有些感慨:“是挺好。”
当年被赶出医官院,他多年不曾也不敢行医,未曾想到有生之年还有为人施诊的机会。西街街邻不知他往事,他在杜长卿的医馆里为人行诊,有时候来瞧病的病人贫苦,他便不收诊银,杜长卿见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令人唏嘘的是,多年以前他一心想通过春试进入翰林医官院,偏偏在如今潦倒一无所有之时,方才得行祖上多年之教诲——
“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尤见其仁且廉也。”
世事弄人。
收回思绪,苗良方看向陆曈,神色有些担忧:“小陆你呢……进了医官院后,可有被人为难?”
平人医工初进医官院,会受到什么样的区别待遇,苗良方比谁都清楚。当年的他亦有不平之心,何况陆曈这样年轻娇弱的姑娘。
“没有。”陆曈摇头,“医官院一切顺遂,并无她事发生。”沉默了一下她才继续说道:“只是答应苗先生的事,现下还无法兑现,初入医官院,行事不好冒险。”
她说的是对付崔岷一事。
闻言,苗良方连连摆手,急道:“我就是想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做此事太过危险,当初之事、《苗氏良方》……都不强求了。”
或许人安逸日子过得好了,便会感谢上天垂怜,对于“仇恨”与“不甘”也会冲淡许多。如今在仁心医馆寻到安定,对于往事也释怀几分。他想,崔岷虽然夺走《苗氏良方》改成《崔氏药理》,可说到底,那药方传给天下医者,也是造福百姓。
此恩通天地,便不必计较芳垂万世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而陆曈,也不必为他一己之私断送大好前程。
陆曈默然。
过了一会儿,她才慢慢开口:“答应先生一事,我一定会做到,这是当初你我做好交易的条件。”
“小陆……”
“其实我今日回来,还有一事想请教苗先生。”陆曈打断他的话。
苗良方一愣:“何事?”
整个西街陷入沉沉夜色,风从更高处刮来,把梅树上挂着的红纱灯笼吹得摇摇晃晃,拉扯着地上凌乱的树影。
陆曈收回视线。
她道:“苗先生当年在医官院做院使多年,医官院医库中各官户记录在册的医案应当都已看过。”
“我想问苗先生,当今太师戚清府上嫡出公子戚玉台……”
“过去曾有视误妄见、知觉错乱之症吗?”
苗良方怔住。
四周阒然无声。
第一百五十五章 登门裴府
淡月藏在屋檐下露出半头,夜风穿过梅树枝隙,把晒在窗前的医籍吹得窸窣乱响。
良久,苗良方开口,望向陆曈的目光满是疑惑。
“小陆,你问这个做什么?”
陆曈沉默。
那一日医官院医库中,她见到了戚玉台的医案。
戚玉台早已及冠,医案记录之言却寥寥无几,或许是因过去多年身体康健并无大碍。然而五年前的深夜,他却请医官院院使崔岷出诊,为他行诊。
医案记载戚玉台是因肝火炽盛而郁结成积,相火内盛以致失调,崔岷所开药方也皆是些疏肝解郁、滋阴生津之材。
但陆曈却瞧见其中还有一些别的药材,多是宁心安神一类。
戚玉台这份医案写得极为简略,几乎没有任何病者情状记录,只有简单几句结果。在那之后近半年时间里,戚玉台又请崔岷为他行诊几次以固根本,但所用药材,亦是多以镇定去癫为主。
加之先前在司礼府,戚玉台自己也亲口承认,多年使用灵犀香安神。
桩桩件件,倒像是长期为稳癫症之行……
然而医案记录有限,此等秘辛又无旁人知晓,便只能回医馆向苗良方讨教。
陆曈抬眼:“苗先生,能告诉我吗?”
苗良方哽了一下。
这位年轻女医官精通各类毒物药理,身份神秘成谜,杜长卿与她相处甚久对她也几乎一无所知,还有银筝,素日里同西街一众街邻谈天说地,唯独对陆曈的事守口如瓶,不发一言。
她怀揣秘密而来,没人知道她想做什么。来到西街不到一年,扶持医馆、制售药茶、春试、进医官院,到最后临走时,还不忘安排仁心医馆各人今后各自归处。
但其实她今年也才十七岁而已。
若他自己有女儿,如今也当就是这个年纪了。
苗良方叹了口气,道:“没有。”
陆曈一怔。
“我离开医官院之前,不曾听说戚玉台有癫症臆病,抑或视误妄见、知觉错乱之症。”
他说得很肯定。
陆曈微微攥紧手心。
没有。
那些医案上的安神药材和长期使用的灵犀香……若无此症,何须长年调养?
何况她当日曾摸过戚玉台的脉,脉细而涩,是血虚神失所养,倒不像是因服用寒食散所致。
只是单看戚玉台言行举止,确实与寻常人无异。
莫非……
是她想岔了?
正想着,耳边传来苗良方的声音:“不过你这么说,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事。”
“先生请说。”
“我离开医官院时,戚玉台还是个半大孩子,他的事我不甚清楚。但是十多年前,我曾给戚玉台母亲行诊……他母亲,是有妄语谵言之症。”
陆曈猛地抬头:“什么?”
苗良方道:“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苗良方刚当上医官院院使不久。
他医术出众,颇得皇家人喜爱,又有“天才医官”的名头在身,不免有几分得意。朝中老臣大官有个头疼脑热的常常拿帖子来请他,有时候忙起来了,也不是人人都能请得动的。
有一日苗良方接了个帖子,是戚清府上的。
当年戚清还不如现在这般权倾朝野、只手遮天,戚家人来得急,只说戚夫人病重,请苗良方赶紧去瞧瞧。
苗良方便提起医箱匆匆去了戚府。
戚夫人是戚清的第二任妻子。
戚清早年间有位夫人,身体不好,早早就去了,也没留下一儿半女。戚清直到中年才娶了这房继室,是礼部尚书仲大人的小女儿,比戚清小了近二十岁。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
- 导航
- 设置
- 字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