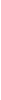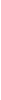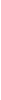| 上一章 | 目录 | 下一章 |
这半月来,他每日晨起去司礼府,黄昏归家。外人眼中看来,一切已恢复原位。
戚玉台却知其中煎熬。
从前父亲虽也管束他,但去司礼府时,尚能寻得一两丝喘息机会。如今却不然。
自打他病愈出门后,戚清便派贴身小厮并护卫守着他。去司礼府也一道,表面同外人说是还需煎药补养身体,实则戚玉台自己心知肚明,父亲分明是监视。
怕他再度发病,怕他大庭广众之下又犯起疯病来,丢了戚家的脸,才让人一步不离跟随,若有意外,即刻将他带回府去,保全戚家颜面。
颜面。
戚玉台自嘲地冷笑一声。
外头那些风言风语他不是没听到,父亲一向爱惜名声,如今他在胭脂胡同被人当笑话猴戏一般观赏,父亲恼怒失望可想而知。
一想到这些,戚玉台就觉脑子生疼,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中炸开。越是如此,越是怀念被一把大火烧毁的丰乐楼。
他又想服散了。
只是眼下父亲看他看得更严,别说服散,连单独出门的机会也没有,只能作罢。
罢了,等后日得了机会,让华楹想法子帮他出门一趟解解闷好了,他这样想。
想到戚华楹,不免就想到了那个令妹妹伤心的罪魁祸首女医官。
恰好仆人送来煎好新药,戚玉台就问:“近来那个陆曈如何?”
若没有丰乐楼撞上那场大火,他早已开始收拾那个低贱医女了。穷街巷口出来的贱人,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让戚家的掌上明珠伤心,纵然有裴云暎护着,他也要想法子叫对方丢一层皮。
谁知突逢意外,耽误时日,倒是让那女人多蹦哒了几日。
身侧仆人回道:“回少爷,陆曈已离开医官院了。”
戚玉台拿药碗的手一顿,抬起头来。
“什么?”
仆人垂首,将近些日子医官院发生之事尽数道来。
言毕,戚玉台喃喃:“竟离开了。”
他还没开始动手,陆曈就已不在?
这或许是崔岷动的手,但裴云暎身为陆曈的靠山,竟也没阻拦?
不对,应当是阻拦的,否则陆曈既敢给崔岷泼脏水,这时候理应早就被彻底赶出医官院,或是挨板子,不会只停职三月。
崔岷还是有所忌惮。
戚玉台神色不屑,不过很快,又高兴起来。
这样也好。
陆曈在医官院时,皇城里有裴云暎盯着,还有那个纪珣,有些事倒是不好动手。
如今流落西街,西街到处都是平人,鱼龙混杂之地,想要对她动手轻而易举,比在医官院更方便。
思及此,戚玉台便舒心起来,连平日觉得苦味难当的汤药,此刻看着也顺眼几分。
“好。”他抬起因生病苍白的脸,略显青黑的眼睛在这一瞬,闪着莫名的光,竟有几分瘆人。
“也算好消息。”
他一面说,一面伸手拿起托盘上的药碗。
乌褐色汤药粘稠,盛在瓷白药碗中,越发显得像摊腐臭淤泥,甫一凑近,苦气顿时盈满鼻腔。
良药苦口,可这药苦的,比之毒药更甚。
戚玉台暗暗骂了一句崔岷,仰头闭着眼,将碗中汤药饮尽。
第一百九十九章 再度发病
夜深了,园中起了层白露。
白露叫夏末的暑夜多了一丝清寂,再过几日就要立秋。
府中安静,长廊有人提灯走过,隐约灯色在夜里忽明忽暗,若翩飞萤虫,停在一处房门跟前。
崔岷推门走进书房。
屋中灯亮了起来。
四周渐被照亮,长桌上摆着几册医籍,日日打扫被清扫得很干净,墨砚都是上等的,桌角摆着一只绿玉竹盆栽,成色鲜亮,十分古雅。
书房很大,看似简致,实则所摆器物陈设,皆是十分讲究。
他在桌前坐了下来。
青玉盘铜座烛台里,微晃的火苗照在他脸上,照亮眼角渐生的沟壑,照亮鬓边几星微白,竟多几分从前未有的沧桑。
崔岷安静看着四周。
这书房是他亲自令人建好的。
他年少时,于药铺给人做伙计,那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更勿提书房。药铺关门后,在柴房里铺张席子,睡觉吃饭,读书认字都在里头。
柴房,就是他的书房。
那不算个好地方,夏日闷热,冬日冰凉,席上常生跳蚤惹得浑身发痒,有时天气暖了,夜里还会有老鼠从身上爬过。
那时他便憧憬,若将来有了自己的屋子,若能在盛京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一处自己的书房,不必太大,只要能装得下他的医书,摆得下一方桌椅就好了。
后来他做了院使,渐渐攒下银钱,在盛京买下宅邸的第一时间,便先让工匠搭制了这间书房。
宽敞、明亮,满架医书,窗前好风景。
比他少时憧憬的更胜百倍。
风吹得院中树影摇晃。
崔岷紧了紧身上外裳。
说来奇怪,他少时睡柴房时,每日吃得粗陋,住得糟糕,偏偏睡得颇好,哪怕夜里漏雨,照样一觉到天明,只恨每日睡的时辰不够多,不能多休憩片刻。
反倒是如今有了大宅子后,软绸榻,点熏香,夏日凉冰,冬日暖炭,却时常失眠不寐。纵是躺在榻上,常半夜睡意毫无。
譬如今夜,他又睡不着了。
崔岷揉了揉额心。
或许,他是真的老了。
书房门发出一声轻响,仆从自外头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碗汤药。
崔岷看了碗中褐色汤药一眼,问:“别吵醒夫人少爷。”
“老爷放心。”仆从道:“夫人少爷都睡下了。”
崔岷点头,伸手接过仆从手中汤药。
这是他给自己开的药方。
戚玉台突犯癫疾,近月余时间,他在太师府尽心熬力,夜里在医官院辛苦至清晨。
他已许多年不曾这般劳累过度,先前还勉强支撑,戚玉台病愈后,才渐渐显出倦怠乏力之症。
崔岷知自己损伤心脾,是以气血乏源,心神失养,是以日日让下人熬煮养心安神的保元养心汤养复。
虽然效用并不算很好。
他抬手,将碗中汤药一饮而尽,掏出丝帕擦拭唇边药汁,忽而想到什么,问:“陆曈近来可有动向?”
陆曈离开医官院也有些日子了。
这些日子,医官院并无他事发生。纪珣和林丹青来问过几次,皆无功而返。
明面上,陆曈只得到停职的惩罚,已是他网开一面。
仆从回:“陆医官回到西街后,一直在仁心医馆坐馆。今日医馆开张五十年,裴殿帅、纪医官和林医官都去西街道贺了。”
“仁心医馆?”
崔岷微微皱眉。
他知道这个医馆。
当初点陆曈进春试红榜第一时,他就已让人打听过陆曈的底细。
陆曈是苏南人,从外地来盛京投奔亲眷,不知为何流落西街,因有一点医术,遂在西街坐馆。
仁心医馆是个破落医馆,东家杜长卿是个纨绔,因陆曈的出现,小医馆起死回生。这医馆里除了杜长卿外,还有一个伙计和陆曈的丫鬟,陆曈进了翰林医官院后,医馆又招了个坐馆的平人老大夫。
一群杂草,乌合之众。
偏偏得裴云暎和纪珣另眼相待。
崔岷冷笑一声。
平人在皇城生存,总要寻一座靠山,对女子来说,没有什么比攀高枝更容易的了。
陆曈很聪明,所以在纪珣和裴云暎之间游走,将两位天之骄子耍得团团转。
但她又很愚蠢,否则也就不会当着众医官的面,不知死活地举告自己偷窃药方罪名。
空了的药碗拿在手上,碗壁有浅浅汤药痕迹,干涸附在白瓷上,如洗不掉的污瑕。
崔岷低头望着,目色闪过一丝轻蔑。
他是对裴云暎和纪珣有所忌惮,但,如今戚玉台的癫疾,反而成了他的保命符,就算为了戚玉台,戚太师也不会让他出事。
打狗也要看主人,陆曈背后有人,他又何尝不是?
各凭所仗而已。
他与陆曈,都是权贵的玩物,一条狗罢了。
正想着,冷不丁右眼皮跳了一下。
崔岷伸手,按住眼皮。
这几日,隔三差五他眼皮都会跳几下,崔岷总觉不安,好似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戚玉台却知其中煎熬。
从前父亲虽也管束他,但去司礼府时,尚能寻得一两丝喘息机会。如今却不然。
自打他病愈出门后,戚清便派贴身小厮并护卫守着他。去司礼府也一道,表面同外人说是还需煎药补养身体,实则戚玉台自己心知肚明,父亲分明是监视。
怕他再度发病,怕他大庭广众之下又犯起疯病来,丢了戚家的脸,才让人一步不离跟随,若有意外,即刻将他带回府去,保全戚家颜面。
颜面。
戚玉台自嘲地冷笑一声。
外头那些风言风语他不是没听到,父亲一向爱惜名声,如今他在胭脂胡同被人当笑话猴戏一般观赏,父亲恼怒失望可想而知。
一想到这些,戚玉台就觉脑子生疼,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中炸开。越是如此,越是怀念被一把大火烧毁的丰乐楼。
他又想服散了。
只是眼下父亲看他看得更严,别说服散,连单独出门的机会也没有,只能作罢。
罢了,等后日得了机会,让华楹想法子帮他出门一趟解解闷好了,他这样想。
想到戚华楹,不免就想到了那个令妹妹伤心的罪魁祸首女医官。
恰好仆人送来煎好新药,戚玉台就问:“近来那个陆曈如何?”
若没有丰乐楼撞上那场大火,他早已开始收拾那个低贱医女了。穷街巷口出来的贱人,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让戚家的掌上明珠伤心,纵然有裴云暎护着,他也要想法子叫对方丢一层皮。
谁知突逢意外,耽误时日,倒是让那女人多蹦哒了几日。
身侧仆人回道:“回少爷,陆曈已离开医官院了。”
戚玉台拿药碗的手一顿,抬起头来。
“什么?”
仆人垂首,将近些日子医官院发生之事尽数道来。
言毕,戚玉台喃喃:“竟离开了。”
他还没开始动手,陆曈就已不在?
这或许是崔岷动的手,但裴云暎身为陆曈的靠山,竟也没阻拦?
不对,应当是阻拦的,否则陆曈既敢给崔岷泼脏水,这时候理应早就被彻底赶出医官院,或是挨板子,不会只停职三月。
崔岷还是有所忌惮。
戚玉台神色不屑,不过很快,又高兴起来。
这样也好。
陆曈在医官院时,皇城里有裴云暎盯着,还有那个纪珣,有些事倒是不好动手。
如今流落西街,西街到处都是平人,鱼龙混杂之地,想要对她动手轻而易举,比在医官院更方便。
思及此,戚玉台便舒心起来,连平日觉得苦味难当的汤药,此刻看着也顺眼几分。
“好。”他抬起因生病苍白的脸,略显青黑的眼睛在这一瞬,闪着莫名的光,竟有几分瘆人。
“也算好消息。”
他一面说,一面伸手拿起托盘上的药碗。
乌褐色汤药粘稠,盛在瓷白药碗中,越发显得像摊腐臭淤泥,甫一凑近,苦气顿时盈满鼻腔。
良药苦口,可这药苦的,比之毒药更甚。
戚玉台暗暗骂了一句崔岷,仰头闭着眼,将碗中汤药饮尽。
第一百九十九章 再度发病
夜深了,园中起了层白露。
白露叫夏末的暑夜多了一丝清寂,再过几日就要立秋。
府中安静,长廊有人提灯走过,隐约灯色在夜里忽明忽暗,若翩飞萤虫,停在一处房门跟前。
崔岷推门走进书房。
屋中灯亮了起来。
四周渐被照亮,长桌上摆着几册医籍,日日打扫被清扫得很干净,墨砚都是上等的,桌角摆着一只绿玉竹盆栽,成色鲜亮,十分古雅。
书房很大,看似简致,实则所摆器物陈设,皆是十分讲究。
他在桌前坐了下来。
青玉盘铜座烛台里,微晃的火苗照在他脸上,照亮眼角渐生的沟壑,照亮鬓边几星微白,竟多几分从前未有的沧桑。
崔岷安静看着四周。
这书房是他亲自令人建好的。
他年少时,于药铺给人做伙计,那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更勿提书房。药铺关门后,在柴房里铺张席子,睡觉吃饭,读书认字都在里头。
柴房,就是他的书房。
那不算个好地方,夏日闷热,冬日冰凉,席上常生跳蚤惹得浑身发痒,有时天气暖了,夜里还会有老鼠从身上爬过。
那时他便憧憬,若将来有了自己的屋子,若能在盛京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一处自己的书房,不必太大,只要能装得下他的医书,摆得下一方桌椅就好了。
后来他做了院使,渐渐攒下银钱,在盛京买下宅邸的第一时间,便先让工匠搭制了这间书房。
宽敞、明亮,满架医书,窗前好风景。
比他少时憧憬的更胜百倍。
风吹得院中树影摇晃。
崔岷紧了紧身上外裳。
说来奇怪,他少时睡柴房时,每日吃得粗陋,住得糟糕,偏偏睡得颇好,哪怕夜里漏雨,照样一觉到天明,只恨每日睡的时辰不够多,不能多休憩片刻。
反倒是如今有了大宅子后,软绸榻,点熏香,夏日凉冰,冬日暖炭,却时常失眠不寐。纵是躺在榻上,常半夜睡意毫无。
譬如今夜,他又睡不着了。
崔岷揉了揉额心。
或许,他是真的老了。
书房门发出一声轻响,仆从自外头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碗汤药。
崔岷看了碗中褐色汤药一眼,问:“别吵醒夫人少爷。”
“老爷放心。”仆从道:“夫人少爷都睡下了。”
崔岷点头,伸手接过仆从手中汤药。
这是他给自己开的药方。
戚玉台突犯癫疾,近月余时间,他在太师府尽心熬力,夜里在医官院辛苦至清晨。
他已许多年不曾这般劳累过度,先前还勉强支撑,戚玉台病愈后,才渐渐显出倦怠乏力之症。
崔岷知自己损伤心脾,是以气血乏源,心神失养,是以日日让下人熬煮养心安神的保元养心汤养复。
虽然效用并不算很好。
他抬手,将碗中汤药一饮而尽,掏出丝帕擦拭唇边药汁,忽而想到什么,问:“陆曈近来可有动向?”
陆曈离开医官院也有些日子了。
这些日子,医官院并无他事发生。纪珣和林丹青来问过几次,皆无功而返。
明面上,陆曈只得到停职的惩罚,已是他网开一面。
仆从回:“陆医官回到西街后,一直在仁心医馆坐馆。今日医馆开张五十年,裴殿帅、纪医官和林医官都去西街道贺了。”
“仁心医馆?”
崔岷微微皱眉。
他知道这个医馆。
当初点陆曈进春试红榜第一时,他就已让人打听过陆曈的底细。
陆曈是苏南人,从外地来盛京投奔亲眷,不知为何流落西街,因有一点医术,遂在西街坐馆。
仁心医馆是个破落医馆,东家杜长卿是个纨绔,因陆曈的出现,小医馆起死回生。这医馆里除了杜长卿外,还有一个伙计和陆曈的丫鬟,陆曈进了翰林医官院后,医馆又招了个坐馆的平人老大夫。
一群杂草,乌合之众。
偏偏得裴云暎和纪珣另眼相待。
崔岷冷笑一声。
平人在皇城生存,总要寻一座靠山,对女子来说,没有什么比攀高枝更容易的了。
陆曈很聪明,所以在纪珣和裴云暎之间游走,将两位天之骄子耍得团团转。
但她又很愚蠢,否则也就不会当着众医官的面,不知死活地举告自己偷窃药方罪名。
空了的药碗拿在手上,碗壁有浅浅汤药痕迹,干涸附在白瓷上,如洗不掉的污瑕。
崔岷低头望着,目色闪过一丝轻蔑。
他是对裴云暎和纪珣有所忌惮,但,如今戚玉台的癫疾,反而成了他的保命符,就算为了戚玉台,戚太师也不会让他出事。
打狗也要看主人,陆曈背后有人,他又何尝不是?
各凭所仗而已。
他与陆曈,都是权贵的玩物,一条狗罢了。
正想着,冷不丁右眼皮跳了一下。
崔岷伸手,按住眼皮。
这几日,隔三差五他眼皮都会跳几下,崔岷总觉不安,好似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
- 导航
- 设置
- 字号
-
- +